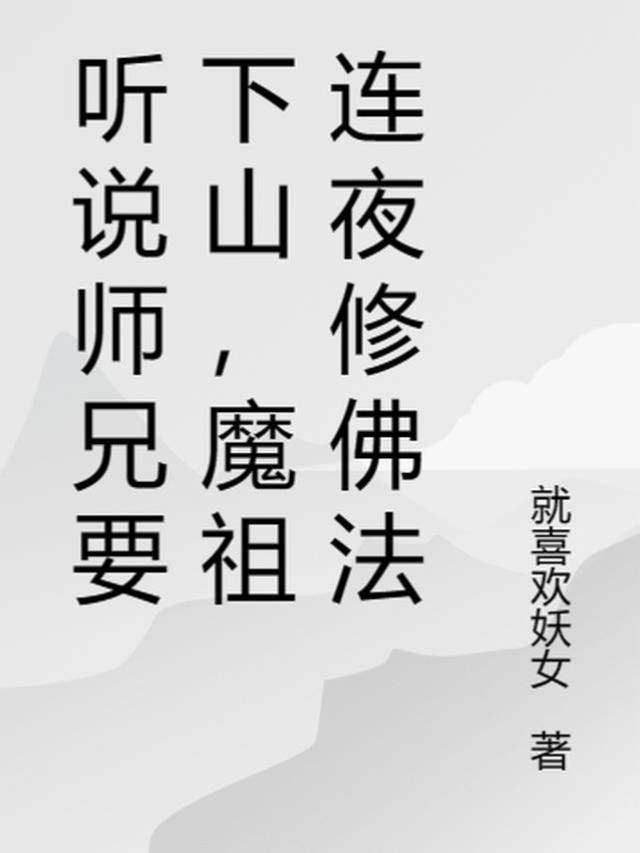《仙界豔旅》 第166章 洗了她小內內
華燈初上,滿街霓虹。
曉曉和小梅高高興興地將忙活了一個多小時才燒好的飯菜擺上了桌子,然後大快朵頤。
“曉曉,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你爲什麼又不洗服了吧?”小梅邊往裡送飯邊問。
曉曉只是呵呵笑著不答,而且還笑彎了腰。
小梅夾起一筷子菜朝張大的塞過去:“我看你真的是中邪了,吃飯吧!”
曉曉躲開小梅筷子的襲擊,還是捧著肚子大笑:“梅梅,呵呵……我……我實在是有些說不出口啊……那個……我的服都被他洗好了……哈哈哈哈……我……”
小梅一聽,也不由得大笑了起來:“怎麼?你還得了一個免費勞力啊,哦……你的服裡面肯定還有吧?”
曉曉滿臉緋紅,只以手掩住笑個不休。
“曉曉,我建議你先到臺上去笑個夠再回來,免得等下吃起來時會噴飯,那這桌好菜可就白做了。”小梅地喝了一口湯,接著說:“讓個陌生男人給你洗,難怪笑得那麼甜。”
“唉!你說什麼呢?那也是因爲我把兩隻水桶佔了,他沒工再洗他的服,才被著幫我洗的嘛!誰知道他今天也要洗服嘛!”曉曉忙做出合理而且不容置疑的解釋。
小梅歪著腦袋,做出苦思狀:“我說曉曉,以後你有服要洗了,就這麼幹,都用不著自己手了。”
“好啊,那你的服也拿過來吧,越多越好,讓他也幫你洗洗。”
兩個子吃吃地笑作一團,大門卻忽然“呀”地一聲開了,一個白白白鞋的男人走了進來。
再一看他臉上那一副黑邊眼鏡,兩人差點跌倒,來人不正是們坐電梯時遇見的那個男子嗎?
Advertisement
小梅不自口而出:“你?怎麼是你啊?”
男子平靜地打量了小梅和曉曉一眼,微微笑了笑:“打擾兩位吃飯了,我是剛住進來的,兩位都住在隔壁嗎?”
二見他那平靜無比的微笑,加上他那細而的聲音以及十分禮貌的話語,反而有些不自在起來。
“哦!我是,不是!”曉曉站起來說:“你來了兩天,我沒能向你打聲招呼,不好意思啊!”
男子輕輕將門關上了,擺了擺手說:“失禮的是我,你這麼說我才真的難爲呢!”
小梅留意著這男子,發覺他雖然上談吐十分自然,但是作卻是十分地拘束,不像平常所見到的男人那樣大大咧咧,倒有幾分姑娘家纔有的矜持,於是不由得心裡涌起一種說不清的好。
“帥哥!請坐!”曉曉早挪了一條凳子過來,雙手做出請的作來。
男子笑了笑:“兩位太客氣了,我剛在外面吃過飯,就不打擾兩位用餐了。”
小梅見他這般,更是覺得這男子十分害臊,倍有趣:“帥哥,賞個臉嘛,至也讓我們認識一下,以後你和曉曉都住在這裡,連對方名字都不知道怎麼行呢?”
男子稍稍猶豫了一下,緩緩走近凳子坐了下來,曉曉早起添碗筷去了。
“我顧小梅,你我小梅吧!這是我死黨曉曉!你以後要多多照顧哦!”小梅笑嬉嬉地說。
曉曉邊往碗里加飯,邊眼打量這個男子,他雖然不是很帥氣,但是那清秀的面龐上出一非常見的氣質,那裡面似乎包含著憂鬱、真誠、睿智等等,這種氣質與他二十來歲的年齡不太相稱,但又說不清哪裡不合適。總之這個人看起來,雖然沒有令人眼睛著迷的地方,但那整個人上出的一種無法形容的東西,卻能地到人的心靈。對於看慣酒之徒的來說,這樣的男人的確令有著特殊的覺。
Advertisement
“我姓司馬,名長空。”男子託了託眼鏡,淡然笑道。
曉曉接道:“司馬長空,好奇怪的名字,不過也很有詩意啊!”說著話的當兒,把碗筷也放到了司馬長空的面前。
司馬長空衝點了點頭:“謝謝!不過我確實吃過飯了,這回可能得撐著了。”
曉曉抿了抿說:“我的服是你幫我洗的吧?”
司馬長空聞言臉上竟然微微一紅,口中應了一聲:“嗯!我也是需要用桶,所以……”
這回換曉曉不好意思了:“實在對不起,我把你的桶都佔用了,還累得你幫我……真的謝謝你了!”
小梅來勁了,衝著司馬長空嬉嬉直笑:“我們家曉曉說了,以後洗服都不用自己手了,我也打算沾的,把服拿過來呢!”
司馬長空也不由得哈哈笑了出來:“可以,不過每個月收你們兩百塊,幹還是不幹?”
小梅歪了歪頭,出手指做著掐算狀:“嗯,兩百塊,價錢合理,買賣公道,了!”
曉曉紅著臉瞪了一眼:“梅梅,正經點好不好?”
小梅吃吃地笑個不停:“看你急的,反正你的老底都讓他看到了,還有什麼好害臊的啊?”
曉曉在桌底下踹了一腳,已經不好意思再去接司馬長空的目了。
“看你都快要哭了,饒了你吧!哦對了,司馬長空,請問你多歲了?”小梅知道曉曉被洗事件一弄,不好意思面對司馬長空了,所以便當起了主人來。
司馬長空雙手互著著指節,發出“咔咔”的骨關節脆響,口中接道:“今年二十四了,你們呢,看看該你們姐姐還是妹妹!”
Advertisement
曉曉總算找到打破尷尬的話題了,搶著說:“我二十五歲,小梅跟你一樣二十四,就是不知道你們的月份,小梅是六月份的,你呢?”
司馬長空神似手輕鬆了許多:“這麼說來,兩位都可以當我姐了,我是十二月份出生的。”
這樣的一個年齡調查,三人都覺自在了許多,小梅更是興:“好啊好啊!我最喜歡給別人當姐姐了,樓弟弟,以後你可要聽姐的話哦!”
“去去去!一天到晚就知道損人!樓看起來比你多了,你這個姐當著心裡也會發虛的。”曉曉打趣道。
“長空,你在哪裡上班呢?”小梅不理會曉曉,正兒八經地問。
司馬長空輕輕一嘆,又用手託了託眼鏡,不不慢地說:“我沒有工作,只是寫點文章掙點兒飯錢。”
“哇!你是作家啊?”曉曉像發現新大陸一樣了起來。
司馬長空尷尬地一笑:“我不是什麼作家,只是一個網絡寫手,寫些七八糟的東西而已。”
小梅可不依了:“能寫就說明你有才華嘛,唉!你寫的是什麼,能讓我們看看嗎?”
司馬長空搖了搖頭:“還是不看的好,那些東西並不是我真正想寫的,而完全是爲了混口飯吃才胡瞎編的,而且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意義。”
曉曉雙手托腮,雙眼變得十分嫵,看多了那些酒場所的男人的,突然邊冒出一個文縐縐的男子,給的覺當然是非同一般的,雖然那種覺稱不上是什麼一見鍾的兒私類,但是從這個男人的上,的確能嗅出一種清新的覺,在的生命中,這麼文雅的男人還是第一次近距離的接到。
Advertisement
小梅繼續說:“我看你太謙虛了吧,如果你寫的東西一點價值也沒有,怎麼會掙得到錢呢?”
司馬長空正說:“小梅,我真沒有騙你,現在網絡上的小說,本就是文字垃圾居多,只是大家一時消的東西,真的沒有什麼價值的,如果你一定要看,過段時間給你看看我真正用心寫的還有點價值的小說吧!”
“說話算數哦!看你的外表就像一個腹有詩書氣自華的人,我們相信你寫的東西一定不錯!”曉曉這句話倒真是出自肺腑。
司馬長空又輕輕地長嘆了一下說:“好!再過幾天一定給兩位過目,讓兩位提點意見。”
曉曉眨了眨眼睛,輕咬一下脣:“我們哪裡提得上意見啊,就是想看你寫的故事,也好知道一下你的羅曼史啊!”
小梅帶著種崇拜的神問:“長空,你是大學畢業的吧?”
“嗯,我剛畢業一個月,這不,也是剛來到這個城市的。”司馬長空說著這話的時候,臉上明顯地變得十分悽楚。
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一直就沒離開過他那清瘦而白淨的臉,見狀心中也泛起了疑問:“長空,是不是這城市裡有著讓你傷心的事啊?”
這回,司馬長空是微閉著雙目,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纔回答:“這個城市裡真的有個我的故事,我的初友在這裡,我們在這裡快樂相過,不過現在要離開我,我來這裡,也只是希偶爾見見。”
“好癡喔!”小梅認真地盯著司馬長空說。
司馬長空苦笑一下:“這年頭了,癡的人總只有傷的份吧?”
曉曉直了直子:“那你願意告訴我們你的故事嗎?”
“會的,只要你們願意聽,不過現在當務之急是把桌上的飯菜消滅掉,都冷掉了。”司馬長空用筷子指了指一盆菜。
小梅和曉曉都笑了起來:“那你也別客氣,嚐嚐我們的手藝吧!”
司馬長空果然夾了一筷子魚放裡,細細地嚼了一下,點頭說:“嗯,很好吃,改天我也讓兩位嚐嚐我做的清蒸魚!”
“這麼看來你不只會洗服,還會下廚房了,這樣的男人不好找嘍!”小梅吃吃笑著說,同時用眼睛瞟了瞟曉曉。
曉曉當然知道意有所指,尤其是聽到洗服,的臉就一陣發燙,心裡一急,口中道:“小梅……你……”
小梅早低頭專心吃起飯來,好像剛纔的話本不是說的一樣。
司馬長空還是隻淡淡一笑:“吃飯吧兩位,不然真的全冷掉了。”
小梅依舊吃吃笑著夾菜,曉曉紅著臉開始往裡送飯。
狂放的DJ樂曲,狂放的豔舞,狂放的人羣,狂放的夜。
曉曉只覺得自己隨著震天價響的樂曲所做出的每一個妖豔的作,都能夠憾天地,當然更能引起男人們瘋狂的衝。但不管怎麼樣,都覺得自己還是有價值的,至,能夠在這瘋狂之中覺得到自己的存在。
可是令反的是,每次演出完畢之後,都得應付一些男人的糾纏。
“曉曉,不是我不幫你,那位李老闆實在是來頭太大,我們得罪不起啊,你就出一次臺吧?”當曉曉回來化妝室缷妝時,張明苦著一張臉向哀求著說。
曉曉一聽便是火冒三丈:“你去跟我們老闆說,我馬上就走人,不幹了。”氣得往桌子上重重的拍了一掌。
張明聽得一慌,忙陪著笑說:“曉曉,你別這樣,我這就去向老闆求請,讓他出面幫你擋過這一劫吧!”
曉曉別過臉去不理他,張明識趣地退出了房去。
凌晨三點的街道,自然已是車稀人了。
曉曉一淡黃的連,輕盈盈地飄過冷清的街道。
那妙曼的段,那麗的臉龐,使得整條街,整個夜空,都有著說不出的魅力。
的髮在夜風中劃出道道人的弧線。
從喧囂的舞臺走出來,走到這樣寂靜的街道上,令曉曉在這繁華與寂寞之間到了人生的兩極。
此時此刻,沒有必要再爲誰表演,也不必因爲那些齷齪男人而窮於應付。此時此刻,除了那浮華的霓虹以外,那習習的夜風,那真實的寧靜都可以讓愜意地自由。
轉那條小巷子的時候,曉曉便有了一種到家的覺。
這裡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沒有外面的喧囂,而便住在巷子的那一頭。
這條小巷當然不是商業街,兩旁的建築大部分都是租房,是真正的生活小區。
曉曉愜意地和長舒了一口氣。
豈料正在這時,小巷的暗影裡忽然竄出一條黑影來,惡虎一般撲向曉曉,曉曉大驚,張口就呼,然而,還沒等發出聲音來,的便被一隻用力的手給捂住了,同時,另一隻手死死地抱住往旁邊一個公廁裡拖。
意識到將要發生的恐怖之事,曉曉哪肯輕易就範,拼了命地掙扎,拳打腳踢地,可是卻怎麼也掙不過那雙鐵鉗一般的罪惡之手。
只片刻之間,曉曉在掙扎之中掉了小肩包,也被強行拖了男廁之中,也在這時候,另一個男人的聲音響了起來:“小妞,在大世酒我給足你面子,你竟然不買賬,這是你敬酒不吃吃罰酒!”
脖子間一涼,一柄寒閃閃的小刀架在了曉曉的間。
“老實點,不然就宰了你!”那隻罪惡的手慢慢地放開了,曉曉這纔看到兩個男人兇狠地站在面前,一個高瘦個小,滿臉鬍渣,正用刀架在的脖子上。
而另一個卻是個大胖子,肚大如缸,一顆半禿的腦袋夾在雙肩上,他已經沒有了脖子了,蒜頭鼻裡哼出一聲:“他媽的,你也不過是個舞,老子什麼樣的人沒見過,看得起你才你出臺,連了你兩次都不給面子。”
曉曉驚魂未定,聲問道:“你……你是李老闆?”
蒜頭鼻一臉邪笑:“你還不算太笨!”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56 章
少年白馬醉春風
長街有煞,喧鬧嘈雜。手持砍刀的屠夫手起刀落,骨上挑花,賣花鞋的老太針挑燭火,百尺無活,還有一個賣油郎,袖裏藏著十八劍,總望著對麵的包子鋪,那手一撕能換九張臉的小西施。長街盡頭還有一座東歸酒肆,裏麵有個釀酒的小少年,那少年……就真的隻是一個釀酒的。他有酒十二盞,卻無人來喝,店裏永遠隻坐著一個醉醺醺的白衣男,抱著長槍晃悠悠,他說想要買匹馬提上酒,縱馬揚鞭,一醉春風。
61.4萬字8 15856 -
連載340 章

問劍
虞國載乾三年,洢州城下了一場雨。李昂渾渾噩噩醒來,夢見自己的腦袋裏,藏著一把劍。
219.3萬字8 12765 -
連載4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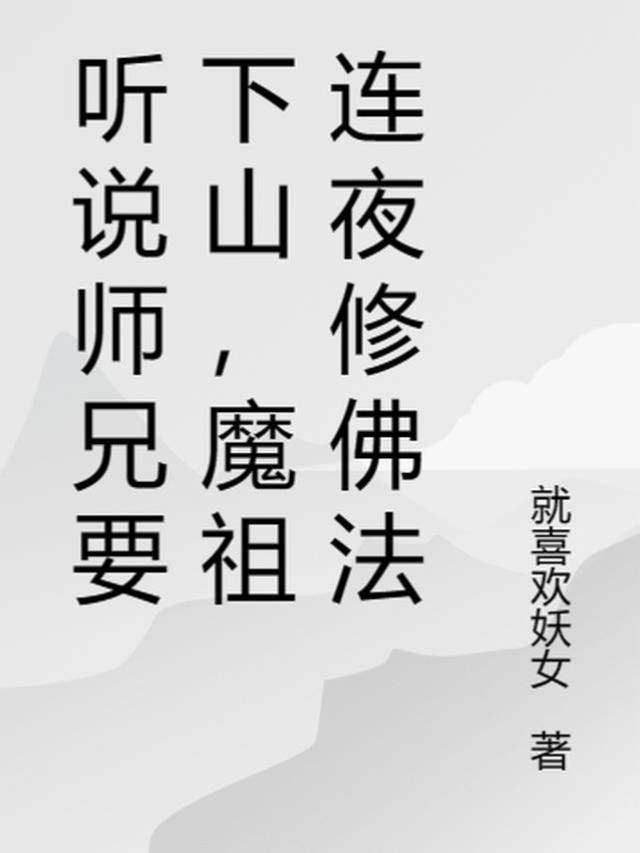
聽說師兄要下山,魔祖連夜修佛法
王慧天,自卑的無靈根患者,劍術通神。自他下山起,世間無安寧!魔祖:“啥?他要下山?快取我袈裟來。”妖族:“該死,我兒肉嫩,快將他躲起來。”禁地:“今日大掃除,明日全體保持靜默,膽敢違令者,扔到山上去”向天地討封,向鬼神要錢。燒一塊錢的香,求百萬元造化。今日不保佑我,明日馬踏仙界……
87.8萬字8.18 148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