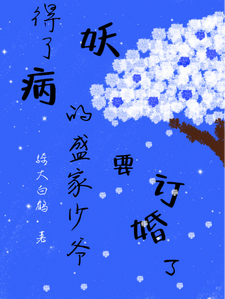《小尾巴很甜》 第45章 四十五點甜
剛掉下來的時候還沒有這麼疼得那麼嚴重, 現在緩沖了幾秒后,兩只手臂才像被燃著一般, 唐溫皺起細眉,眼圈漸漸蓄滿一層淚。
許珩年眸微沉, 一手繞過去輕攬住的腰,另一只手附在的彎下方,毫不費力地將整個人抱了起來。
忽如其來的騰空令唐溫心下一沉, 低呼一聲, 下意識地環住了他的脖子,“你要干嘛?”
“去醫務室。”怕害怕,他刻意放輕了聲音。
站在他后的壯漢聽到這兒,頓時倒吸一口冷氣, 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還是他所認識的那個高冷寡言的部長嗎!!!
正迷茫著, 見許珩年轉,他連忙機靈地躲到一旁,讓出一條道路來。
剛走了兩步, 許珩年發覺董珂一直在后面跟著,沉聲打斷:“我來就好。”
董珂一邊亦步亦趨地跟著, 解釋說:“有一個生跟著會方便一點。”
“不用了。”他走到門口側過來,語氣冷淡,臉上看不出任何表。
Advertisement
董珂翳了翳,漸漸停住了腳步。
剛巧是晚自習的時間,走廊上沒有一個人,唐溫害地拽了拽他的襟, 將臉埋在他的頸窩里,小聲嘟噥:“讓我下來自己走吧。”
這可是在學校啊,萬一被老師看見該怎麼說,就算被同學看到,也要七八糟瞎傳一氣吧。
聽到這兒,許珩年低笑一聲,輕輕地說:“你能站得穩嗎?”
拖著的彎,他都能明顯的覺出,還在發抖。
“……”唐溫被他輕飄飄一句話堵得無言以對,想了想,最終還是側過臉去,不再思考這個問題。
醫務室里沒有人,值班的醫生可能是臨時有事離開了。他將放在病床上,從一旁的櫥柜里找出便攜的醫藥箱來。
“只有手臂疼嗎?其他地方有沒有覺摔傷的。”他打開藥箱,依次瀏覽了一遍瓶瓶罐罐上的名稱。
皺著眉了腳,覺腰的部位好像是摔青了,地疼,但是有點不好意思開口,就支支吾吾地說:“還行。”
Advertisement
許珩年輕撇了一眼,出生理鹽水來,用棉棒沾了沾,用眼神示意開袖子。
他小時候跟陸淮琛一起學散打經常會傷,所以也掌握了一些一般傷口的理方法,等將袖子開之后,將沾滿鹽水的棉棒覆在傷口之上,輕輕涂抹。
那覺清清涼涼的,稍微有一點點刺痛,許珩年一直輕托著的臂彎,耐著心,手上的作一輕再輕。
因為隔在袖,并沒有過多灰塵滲進皮之中。
他坐在床沿上,拿出酒瓶來,微蹙了下眉,過手握住冰涼的指尖,溫聲說:“會有點疼。”
不自覺地輕咬了下后槽牙,慢吞吞地開口說:“沒關系。”
許珩年沾了些碘酒,剛落在傷口邊緣的位置,就條件反地了一下手,胳膊有些抖。他重新托住的肘彎,用溫和的語氣盡量轉移著的注意力:“這周三下午學校要大掃除,之后會放假。”
“啊,”碘酒的刺痛燒得頭皮一跳一跳得,眼眶中的淚珠也忍不住地掉落下來,都白了,小心翼翼啞著嗓音回應他:“要放假啊……”
Advertisement
許珩年微垂下去,幫輕輕吹了吹傷口,試圖緩解一下的疼痛。
唐溫咬了咬,怕他太擔心,盡量平穩著自己的聲音說:“那…打掃完后…我們要回家嗎?”
“不回。”他往前湊了湊子,盯著眼睛說。
頭懵懵的,眼睫上還掛著幾滴淚珠,小聲問:“那我們去哪兒?”
許珩年垂下頭來,親了親微的睫,攥著的指尖聲說:“帶你去看電影。”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4 章

項羽重生在校園
項羽重生成了一個因為表白失敗而跳樓自殺的同名世家子弟。“我若重生,誰人可阻?”
89.6萬字8 54615 -
完結61 章

小清歡
全一中的女生都知道,乖戾囂張打起架來不要命的第一名陳讓,對隔壁敏學私立高中的齊歡冇有半點好感。隻是那時她們不曉得,陳讓自己也不曉得——在後來的漫長時光中;她的..
17.6萬字8.43 8044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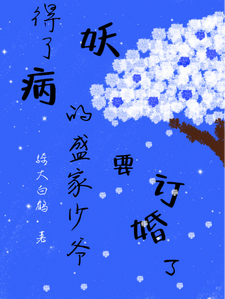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
完結199 章

裝純
蔣馳期剛入學就被偷拍掛在了校論壇上。 男人藉着張神顏臉,被人沸沸揚揚討論了半個多月,一躍成了L大的風雲人物。聯繫方式泄露後, 僅一天,他的微信就被加爆了。 衆多矜持內斂的驗證信息中,有一條格外大膽: “看看你的。” ? — 因爲學業壓力過大,尤簌時常在網上無差別發瘋。 某天,deadline迫在眉睫。尤簌爲了疏解壓力,湊熱鬧給學校的風雲新生髮了句大膽嘴炮,就去洗澡了。 出浴室後,她看見微信多了兩條消息—— 第一條: “對方通過了你的朋友驗證請求,現在你們可以開始聊天了。” 第二條: “看哪?” …… 時經數月的網聊後,兩人第一次“面基”。 考慮到尤簌某些不可言說的屬性,蔣馳期臨出門前特意多穿了件外套。 一路上,尤簌都不太敢說話,蔣馳期以爲她在玩欲擒故縱。 直到指針轉到十點,蔣馳期終於察覺到身旁的女生有了一絲波瀾。 他抱臂等了半分鐘,以爲她終於要暴露本性。接着,他看見了尤簌帽子下紅透的臉。 女生說話都磕磕絆絆,任誰看了都覺得純情得要命。 “不然今,今天就到這裏吧,我還有論文沒寫完…” 蔣馳期:? “你裝什麼純?” 尤簌攥緊衣襬,不敢說話。 “是誰之前說的,遲早給我點顏色看看?” “……”
35.2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