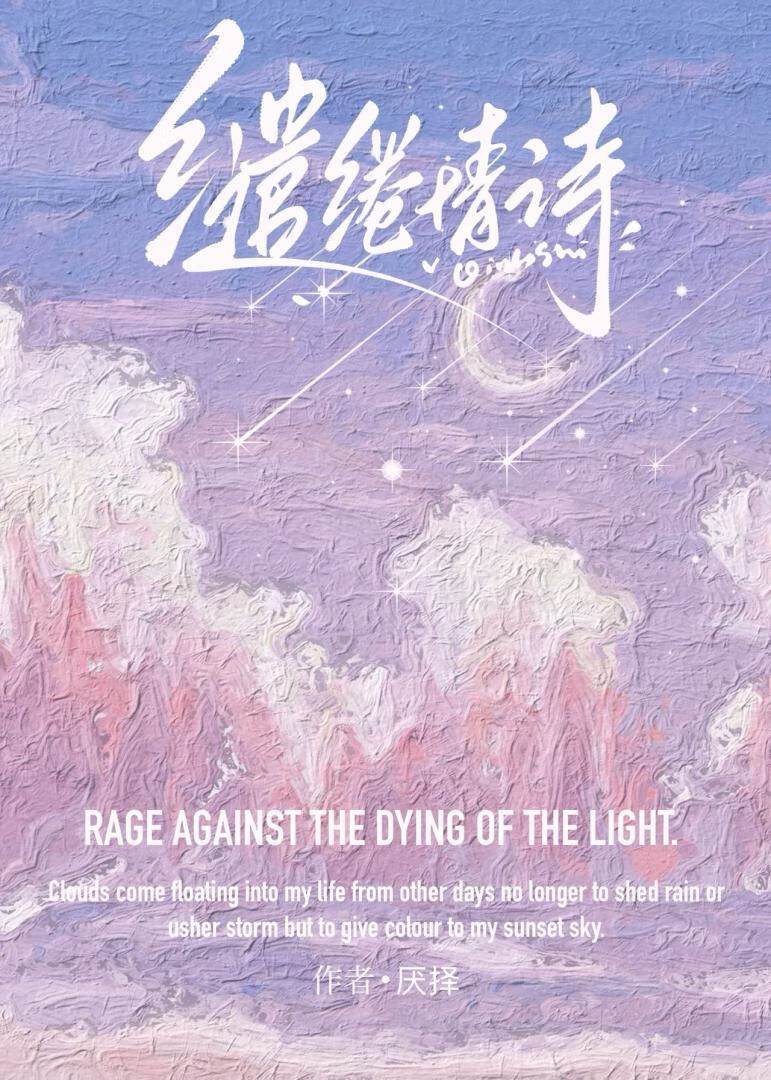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第42章
蘇毓見這沒見過世面的呆樣,角微揚:“這筆還有別的用, 你試試用尾端點點‘青箬谷’。”
小頂依言點了一下, 只聽“噗”一聲, 金筆尾端忽然冒出一團青煙,煙霧凝聚變幻, 變一堆閃著微的青谷粒,接著谷粒中出小芽,芽迅速長大,拔節,結穗,條,開花,然后結出充實飽滿的谷粒,谷粒落下,重新變回一堆谷粒, 最后化作一陣青煙飄散。
小頂睜圓了眼睛,檀口微張,半晌才回過神來, 這也太厲害了!
只不知道這支筆是只能點一本書, 還是別的書也能讀,暗暗思忖, 要是能讀別的書,那麼靈府里那本……
蘇毓仿佛能讀心似的,立即解答的疑:“有字便可用此筆。”
他說著從案頭拿起一塊古樸的木牌遞給:“想看什麼書, 自去藏書塔借。”
小頂接過一看,正是在第一堂心法課上贏來,又以五十萬靈石賣給西門馥的那種木牌,憑此令牌可以出藏書塔的任意一層。
蘇毓叮囑道:“不可再拿去賣了。”
不用他說,小頂也不會再把令牌賣了,當時也是為了還錢不得已。
經他一提醒,倒是想起了當初用令牌換錢的原委,撇開眼,咬了咬,咕噥道:“那時候我不想賣的,要還師尊的債。”
蘇毓:“……”還記仇。
不過一想當初那事,的確是他理虧,便道:“為師難道圖你那點錢?”
小頂輕哼了一聲:“當然不是。”話雖這麼說,臉上的神顯然表達著截然相反的意思。
蘇毓了眉心:“若是圖你錢,后來那三十一萬怎麼會給你免了?”
小頂顯然不相信他的話。
Advertisement
蘇毓冷哼一聲,從案頭拿起一支空白玉簡,填上八十萬,刻上自己的印鑒,沒好氣道:“還你便是,往后別再說我圖你錢了。”
“嗯。”小頂面稍霽,接過玉簡揣在百寶囊里。
挲了一下金筆,在耳邊晃了晃:“師尊,這里面裝的,莫非是你的元神?”
掌門的心法課上講過,修士到了元嬰期,便能擁有元神,元神可以離,像連山君這樣的大能,元神十分強大,只要分出一小片,就能出去替他辦許多事,甚至還能化作分呢。
蘇毓輕嗤一聲:“自然不是,略施小罷了。”以為他的元神是大白菜?隨隨便便就掰一片下來送人?
小頂略微放心,但還是問道:“這里面的聲音,和師尊的元神,沒連著吧?”
頓了頓,蓋彌彰道:“我怕打擾師尊。”
蘇毓抬起眼皮,斜睨一眼,這徒弟倒是比剛來時聰明了點,竟然學會了和他斗心眼子。
他暗暗一哂:“不會,否則你整日用此筆讀書,為師豈不是什麼都不用做了?”
頓了頓道:“別胡思想了,這只是我煉著玩的法,與神魂沒有聯系。”
小頂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那能不能,換個別的聲音?”
師父平常說話便冷冰冰的沒什麼人味,這筆變本加厲,連高低起伏都沒了,更多了幾分生無可的味道。要是能換個中聽些的聲音就好了。
蘇毓起眼皮:“你想換誰的?”
小頂雕玉琢的小臉上一抹淡淡的胭脂,水眸滟滟:“換金師兄的,可以嗎?”金師兄中氣足,說起話來當當當像敲鐘似的,很喜歡。
蘇毓聞言臉便是一黑。
小頂和他相久了,稍微能辨別他的喜怒,忙改口:“那仙子姐姐也可以,或者阿亥,掌門師伯,葉師兄,梅運,大嘰嘰……”
Advertisement
雖然兒子一口一個嘰,但聲氣的還怪好聽。
蘇毓算是聽出來了,總之除了他誰都行。
他面沉似水,眼中的寒簡直能凝冰箭:“不能,只有這種聲音,不想要便還我。”
小頂忙握了筆:“要的要的,不換就不換吧。”筆那麼好,就這一點不足,還是將就一下吧。
蘇毓心口仿佛堵了一團綿絮,再說下去,他懷疑自己會被這小白眼狼氣得平地飛升。
于是他垂下眼,冷漠地揮揮手:“為師有事忙,你自己回屋去玩。”
小頂不得趕回去讀書,飛也似地跑回屋里,關了門。
先拿出抄了一半的千字文,用金筆試著點了點,連山君的聲音響起:“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師父沒騙,果然是有字便能讀。用尾端輕點了一下,照例冒出一煙霧,先是混沌的一團,逐漸分玄和黃兩,兩氣糾纏旋轉,慢慢分開,清氣上浮,濁氣下沉,日月星辰開始閃爍。
小頂點了這個點那個,玩得不亦樂乎,半晌才想起正事,忙潛靈府,拿出那本天書。
不知道怎麼把東西帶進靈府,那本天書也帶不出來,但是可以記住書上的文字,出了靈府寫在紙上便是。當然讀完得立即燒掉,免得留下痕跡。
這段時日跟著碧茶研讀十洲三界男榜,倒是學了一些字,一段中大約有一小半不認識,只要將那些字的形狀記住即可。
的腦袋瓜雖不如碧茶那麼聰明,記卻很是不錯,最擅長依樣畫葫蘆,每回符法考試都能拿高分。
不過片刻,便將第一句話記住,出靈府寫下,再潛進去記下一句,如是反復。
如今有了筆,也不用分什麼輕重緩急了,從頭開始一點點抄便是。
Advertisement
屋子里靜悄悄的,只有筆鋒著紙面,發出春蠶嚙桑般的沙沙聲。
謄抄完第一頁,脖頸和手腕,看了一眼更,花了將近一個時辰。
速度雖然慢,但日積月累,早晚能把整本書讀完,像原先那樣隔三岔五問師父兩個字,讀懂全書恐怕得猴年馬月了。
小頂拿起金筆,正要開始讀,忽然聽得隔壁東軒門簾輕響,是師父回來了。
忙放下筆,師父在隔壁打坐,墻上還有個,修士的耳力又好,若是他聽見,泄了天機,可就壞事了。
思索片刻,把紙疊好,和小筆一起收進百寶囊里,從箱里拿和出換洗的裳和巾櫛,對著墻道:“師尊,我去沐浴啦。”
蘇毓“嗯”了一聲,淡淡道;“這些事不必告訴我。”
小頂:“你可別聽啊。”
蘇毓眉頭跳了跳:“……知道了。”誰稀罕聽你。
不過他耳力過人,就算不刻意聽,浴堂中的靜也會傳到他耳畔,比如傻徒弟嘩嘩的玩水聲,還有那些自己編詞、跑掉能跑到昆侖山的歌謠。
他心好時便由著去,有時候嫌煩,便施個隔音咒,用無形的屏障把聲音隔在外頭。
若是不特意說,他聽了也就聽了,可這麼一說,倒像是他故意聽似的。
蘇毓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既然說了,他也不愿做跌份的事,便即施了個隔音咒,耳邊頓時清靜了。
小頂跑進浴堂,閂上門,坐在浴池邊上,從百寶囊中掏出謄抄的天書,用金筆點了點。
筆中傳出師父冷若冰霜,語調平板的聲音,回在空曠軒敞的浴堂中。
【許多年后,小頂還記得初見連山君時的景。】
小頂點了點“連山君”三個字,師父一板一眼地道:“連山君,道號,本名蘇毓,渡劫期九重境劍修,歸藏派十一代弟子,師承純元道君……”
Advertisement
師父的介紹和他本人一樣枯燥乏味。
小頂了下,忽然起了玩心,掉轉筆又點了一下,金筆尾端“噗”地冒出白霧,頃刻間凝聚一個掌大的小人,手里還拿著一把銀閃閃的長劍。
小人的眉眼和師父一模一樣,眉宇間那子不好惹的勁頭也如出一轍。
小頂把小師父抓起來放在掌心,出食指捋捋小師父的頭頂,小人一橫眉,揮劍便朝劈來,奈何他是煙霧凝,這一劍看著雖狠,實則沒什麼殺傷力,只能撓個。
小頂到十分逗趣,咯咯笑著,屈指在小師父額頭上彈了個腦瓜崩。
小師父一個趔趄,跌坐在掌心,氣得頭頂冒煙,瞬間消失不見了。
自顧自傻笑了一會兒,驀地想起正事要,接著往下點。
【那是一個冬日的黃昏,蜷在黑暗的木箱中,外面傳來廝殺和慘,徹骨的寒冷和恐懼令抱住自己。不知過了多久,外面安靜下來,有輕而沉穩的腳步聲慢慢靠近,的心臟了一團……
就在這時,腳步聲停了下來,箱蓋猛地打開,一下子灌進來,不由覷眼,視野中一片朦朧。
而他就靜靜立在那里,白勝雪,長發如墨,陌上人如玉,公子世無雙。
最先看清的,是他那雙幽黑如深潭的眼眸,里面仿佛埋藏著無盡的悲涼與千年的風霜。只是那一眼,便義無反顧地跌進了那雙眼眸里,仿佛跌進了無盡的深淵……】
講完了眼睛,這書又把連山君從頭到腳講了一遍,眉、鼻子、、下頜、脖子、軀、手……
從頭發到腳后跟,都細細描摹過去,時不時夾雜一點風啊霜啊雪啊冰啊,喋喋不休,聽得小頂直打呵欠。
是他的長相聲音,就占了大半頁,小頂了發酸的手腕子,覺很冤,這麼多字都白抄了。
耐著子聽下去,連山君總算開口了。
【“看著倒是個極品。”】
接著又是一大段,講他聲音怎麼清冷怎麼好聽。
【小頂瑟了一下,想回答,聲音卻像是卡在了嚨里。只是一只卑賤的爐鼎,在高高在上、宛如神祗一般的修士面前自慚形穢。】
小頂“嘖”了一聲,忍不住皺起眉頭,聽聽這什麼話,爐鼎有什麼不好,怎麼就卑賤了?
【俊無儔的男子冷冷地打量了兩眼,出手:“想做我的爐鼎麼?”】
小頂困地撓了撓腮幫子,這開頭怎麼和的經歷不太一樣。
想為了當上連山君的爐子,費了多周折!
接著又是一大段寫他的手,從骨節到指甲,總之就是漂亮得天上有地上無。
偏偏是用他本人的聲音讀出來,怎麼都像是自賣自夸。
【小頂遲疑了許久,終是小心翼翼地站起,鼓起勇氣,將纖細脆弱的小手輕輕放在他手中。輕如鴻的一生,就這麼付了出去。
男人勾了勾角,幽黑的眼眸依舊冰寒如茫茫雪原,眉眼溫:“不用怕。”
說罷,他住纖細的手腕往上一提,另一只手托住只堪一握的纖細腰肢,將抱懷中。】
又是一大段寫連山君的氣味怎麼好聞。
小頂不得不承認,師父上的味道的確好聞的。
但也犯不著這麼翻來覆去寫吧,這一個個字可都是費了老鼻子勁抄出來的。
【小頂不由舒展雙臂,勾住他的脖頸,薄如蟬翼的鮫綃紗里出曼妙的線條,膩如羊脂白玉的,還有若若現的一點淺紅,雪酪上的一點櫻桃,隨著張的呼吸,起伏,微。】
這段小頂就有些看不懂了,用筆點了點“雪酪”和“櫻桃”,原來都是吃的。又用筆尾點了下,看見櫻桃雪酪的樣子,饞得差點沒流下口水。
不由納悶,書里的小頂懷里揣著吃的,那時候怎麼沒有?
【男人的瞳孔微微一,一低頭,竟然將肩頭的細金鏈子抿在雙中,輕輕拉扯,疼得低了一聲,被他托著的后腰卻升起一麻。】
小頂聽得直起皮疙瘩,不由了自己的肩膀,傷口雖然愈合了,但還是對那兩條金鏈子心有余悸。
【男人松開金鏈子,笑容如謫仙般澄澈,又如邪魔蠱人心,薄一掀,吐出的話語近乎殘酷:“若你識趣,我可以考慮多留你幾日。”】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1 章

愛情是糖,甜到憂傷
徐子妗愛了傅斯年二十年,愛到最后把自己殺死。傅斯年病態的愛著那個叫徐子妗的女人把自己逼成了神經病。然而,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是隔著血海深仇,就隔著那座叫沐安安的墳!…
4.7萬字8 7769 -
完結158 章

誘她上榻,爺的小婢女是禍水
【美貌小禍水X玉面羅剎】【雙潔+甜寵+美炸天女主】 南珠是國公府沈家四小姐身邊的小丫鬟,奈何生得禍國之姿,被小姐和夫人針對,竟要將她嫁給瘸腿的矮奴。 為了不被逼著嫁人,南珠只好爬上人人敬畏大少爺的床,主動獻出自己。 第一次獻時,他說:“我救你,并沒想讓你以身相報。” 第二次獻時,他說:“你想好了,不后悔?” 南珠狠下決心:“爺,求爺收了南兒,南兒心甘情愿伺候爺。” 萬萬沒想到,沒想到霽月清風的爺,折騰人的花樣這樣多。 白天,沈燕白教她讀書寫字,教她經商之道。 晚上,沈燕白疼她入髓,與她纏綿至天明。 后來,聽說沈燕白要娶妻,南珠就跑了,第二次被抓回來后,沈燕白瘋了,將她關進金籠中。 “我沈燕白的床這麼好爬麼?” “南兒,上了我的床,生死都是我沈燕白的人,沒有我的應允,哪也休想去。” 在沈燕白這里,無論是世家小姐還是尊貴的公主,都不及懷中這個撒潑的小南珠。 【排雷】 本文背景架空,這里商人有地位,后代可從政,看小說圖一樂子,這本沒有歷史參考價值~ 文中衣食住行都是各朝各代參雜一起。 土狗文學,女主美美美。 非大女主文,沒有重生、沒有穿越
28.3萬字8 96 -
完結65 章

她已經從良好多年
尹采綠穿着破衣爛衫在街頭遊蕩時,被薛家人撿了回去。 薛夫人說她生得像極了自己死去的女兒。 她搖身一變成了侯府的千金小姐,薛家人對她的寵愛卻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 只是將她裝進了一個堆金砌玉的殼,要她學數不清的規矩。 她終於知道薛家人爲何要將她撿回來了。 她代替的那位死去的薛小姐,原來還留有一門皇家的親事,薛家不願放棄這門親,纔將她撿了回來。 外傳薛家千金薛靜蘊是遠近聞名的才女,素有賢德之名,薛夫人要尹采綠無一處不似薛靜蘊。 尹采綠把自己裝得像模像樣時,等來了太子妃的封詔。 太子溫潤,卻生性無慾,薛家人耳提面命:太子妃未必要取得太子寵愛,但家族榮光重若千鈞,在言行舉止、儀態風度間,更要嚴遵宮廷儀範,絲毫不容有失。 薛夫人見她模樣端正,會心一笑:“切記,不可露了馬腳。” ———————— 尹采綠被薛家撿回時,流浪在外已有一段時日了,在那之前,她所居之處,是朱樓綺戶,雕樑畫棟,每日有無數文人雅士、達官顯貴候着她,只爲能得見她一面,一親芳澤。 只可惜後來江南的玉笙樓倒了,媽媽被官府捉了去,她一路向東遊蕩,就到了京城,被薛夫人撿回了家。 討好生性無慾的太子,她的確費了些功夫。 偶然想起薛夫人的吩咐,她收斂些,可下一次還是忍不住,畢竟以往見着男人聲音就會嬌、腰肢就會軟的毛病,一時半會兒改不了呀。 只是……太子新召入京的官員,她不太喜歡。 那是她以往的常客。 某日,她看到從外面回來的太子黑着臉,嚇飛了魂兒。
20.4萬字8 105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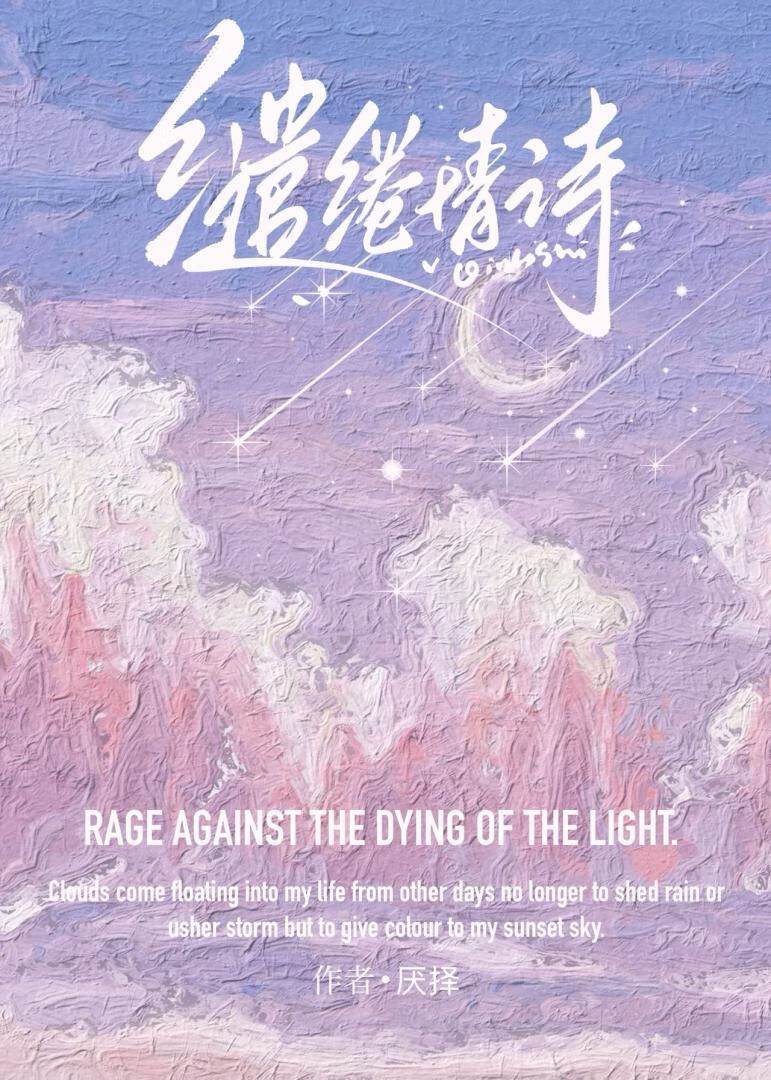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