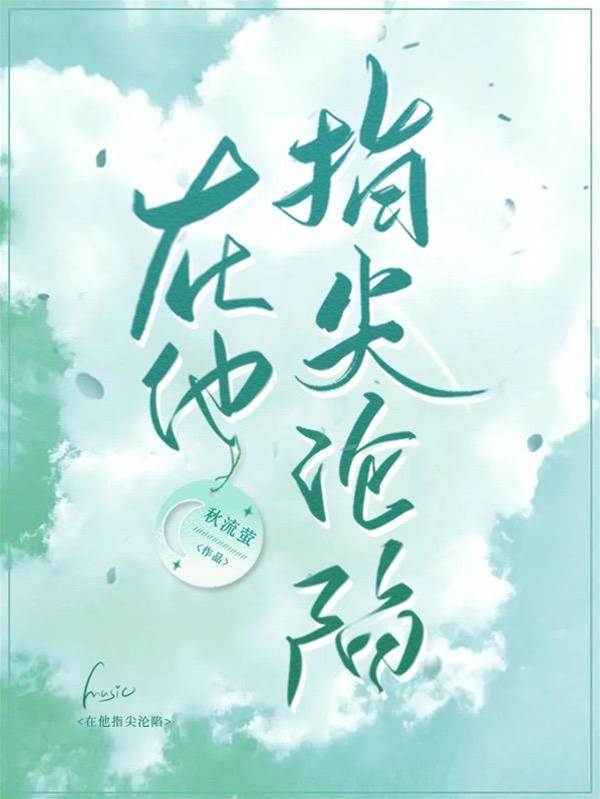《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第24章 (第二更)
迦陵鳥一族是九獄山的土著, 雖然只剩下一窩, 但法力高強,威武霸氣, 只是為鳥類, 頭太小,腦子不大好使。
當年歸藏開宗立派, 祖師欺負大嘰嘰他爺爺沒文化,半哄半騙, 用一萬塊靈石買下了九獄山九峰。
說是不影響他們群妖在外山安居樂業,實則鉆契約的空子, 用河圖石把九獄山的靈氣都引九峰,以至于外九峰靈氣稀薄, 了名副其實的窮山惡水。
大嘰嘰他爺爺花了五百年才回過味來, 知道自己是被騙了。
被雷劫劈死前,老鳥叮囑孫子,第一歸藏派都是孫子, 我們迦陵一族和他們不共戴天。第二爺爺當年吃了沒文化的虧, 你一定要好好學習。
大嘰嘰的畢生志向便是滅了歸藏滿門,把祖業搶回來,然而當年的靈契約束, 外山群妖和歸藏弟子不得互相殘殺,否則就要到靈契之力的嚴懲。
歸藏祖師坑蒙拐騙雖然不地道, 倒也沒有對妖族趕盡殺絕——買靈守山還費錢, 每個月給群妖施舍點靈氣, 就有了一支不花錢的巡山護衛,何樂而不為呢?
因此歸藏弟子和群妖雖然相互看不順眼,但也只能著鼻子搭伙過日子。
云中子是個濫好人,對群妖比歷任掌門都大方,且他本也是妖族,大嘰嘰上喊著要滅了歸藏,但對云中子還是比較滿意的。
但是蘇毓這壞種,簡直比他師祖還不是東西!
大嘰嘰辛辛苦苦攢了好幾百年的天才地寶,被他半搶半騙,掏去了大半。
如今他虎落平,怎麼能被仇家看好戲?
大紅立時閉,黑豆眼骨碌碌一轉,假裝無事發生:“嘰?”
然而覆水難收,份已經暴,再掩飾也無濟于事了。
Advertisement
蘇毓狐疑道:“你怎麼會在肚子里……”
他沒用過爐鼎,也不了解玄素之道,但無論如何這也太超乎常理了,要都這麼作,誰還敢雙修。
大紅眼神發飄,弱氣地“嘰嘰”兩聲,隨即又跳腳大罵起來:“蘇毓你這殺千刀的孫子嘰……”
顯然就是在虛張聲勢,蘇毓冷笑一聲,正要刻薄他兩句,卻見那小爐鼎走上前去,“啪”地照著大紅屁扇了一記。
“大嘰嘰,”小頂虎著臉數落大紅,“不許罵人。”
迦陵鳥大小是個妖王,蘇毓還從未見過他如此狼狽,角不由揚起。
沒高興片刻,只聽那爐鼎又道:“烏,有什麼錯?”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孫子。
蘇毓:“???”
小頂不吭聲還好,一說話,大紅越發氣不打一來,當即暴跳如雷、破口大罵:“你這老巨猾的死人嘰……”
不等他把話說完,又是清脆的“啪啪”兩下。
傀儡人打圓場:“小頂姑娘,大嘰嘰公子還小,慢慢教。”
小頂看著雖綿綿的,卻不是個溺孩子的家長,一手抓著大紅的赤金羽,一手扇他屁:“我是阿娘,再不乖……”
想了想,瞪他一眼:“再不乖,把你吃掉!”
大紅立即偃旗息鼓,能屈能,輕聲細氣地“嘰”了一聲,然后起脖子和短,骨碌碌滾到墻,努力長翅膀遮住眼睛,在那兒不了。
阿亥一陣見:“小頂姑娘,大嘰嘰公子是紙做的,怕是不能吃。”
大紅一聽,立即神抖擻,長脖子,正要接著罵,傀儡人話鋒一轉:“不過丹倒是可以吃,你們活人吃這個很補的。”
大紅天真爛漫地“嘰”了一聲,又把脖子了回去。
Advertisement
蘇毓知道其中定有貓膩,問迦陵他是不會說的,便問小頂:“你肚子里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小頂大不解地歪歪頭:“因為我,吃了,腚男人的,大鳥。”已經告訴過他們不止一次了呀。
蘇毓了眉心:“你把前因后果說清楚。”
小頂便把那天夜里發生的事敘述了一遍,在門派里生活了半個多月,說話已經比一開始順溜了不,這回沒人打斷,沒費多大勁,就把事說清楚了。
蘇毓聽完,半晌說不出話。
吃了大鳥。
是真的吃了,吃了,吃了大鳥。
然而整件事看似真相大白,實則撲朔迷離,充滿了謎團。
迦陵鳥每三百年換一次,換期持續七七四十九日,在此期間妖丹融化,散經脈,不止是換,約等于整只鳥胎換骨一回。
這段時間他的妖力大幅降低,大約只有平日的一兩。
然而畢竟是只千年老鳥,即使只剩一功力,也不是僅憑他裳里的咒能克制住的。
蕭頂撇開爐鼎不說,就是個凡人,怎麼輕而易舉就讓妖王昏厥了?
其次,吃下去的老鳥為何會變蛋?甚至重新凝聚出了妖丹。
據他所知爐鼎可沒有這種奇效。
莫非不是一般爐鼎?
正思忖著,蔣寒秋一聲怒罵打斷了他的思緒:“這都能想歪,你天都在想些什麼?沒想到你心思這麼齷齪!”
蘇毓:“……”還不是你師父先想歪的。
他被師侄一打岔,思路一拐彎,拐到了這小爐鼎上。
眼下他終于相信,這爐鼎是真傻,雖然天嚷嚷著要給這個那個做爐鼎,實際上本不通男之事。
許是綁的人還未來得及教——也或者是故意讓保持蒙昧無知,似乎確有一些買家喜歡天真如稚的爐鼎,自己回去調教。
Advertisement
蘇毓最見不得這些下流污穢之事,再看那爐鼎,心不有些復雜。
原本以為是蓄意引,原來都是無心之舉。
是他想多了。
連山君斷斷不愿承認是自己自作多——這一切只是世事弄人。
蔣寒秋看了眼蹲在墻角苦口婆心教育大紅的小頂:“這孩子顯然是把那……玩意兒當了孩子,是你惹出來的事,你就說怎麼辦吧。”
蘇毓回過神,冷聲道:“不見得讓我去教生孩子是怎麼回事。”
蔣寒秋一噎,隨即道:“你休想用你的骯臟心思玷污小頂。”
便即捋起袖子,著頭皮自己上。
把小頂帶到一邊,看了一眼大紅,溫聲解釋:“小頂,這只……鳥,不是你的孩子。”
小頂一愣:“可是,他是我生的,呀?”
蔣寒秋:“……孩子不是這麼生的,你吃下去的鳥做迦陵,是外山的妖王。”
小頂仍舊不甘心:“那,孩子是,怎麼生的?”
蔣寒秋避開無邪的視線,尷尬地咳嗽兩聲,含糊道:“要夫妻或是道才能生,也不是從里生,等你嫁了人就知道了。”
小頂看了一眼大紅,低下頭訥訥道:“我知道了……”
抱著膝蓋,眉眼低垂,眼圈漸漸泛紅。
蔣寒秋哪里見得這個,連忙改口:“不過反正他也在你肚子里呆過,你要把他當兒子也未嘗不可。”
大嘰嘰:“???”
小頂驀地抬頭,淚盈盈的大眼睛里閃著欣喜的:“真的?”
蔣寒秋毫無原則:“當然,從今往后他就是你兒子,誰敢有意見,先來問問我的劍。”
小頂眼淚,破涕為笑:“那我明日,能騎大嘰嘰,去學堂啦?”
蔣寒秋:“……”
Advertisement
蘇毓:“……”
鬧了半天,這傻子大概本不知道兒子是用來做什麼的。
傀儡人面憂:“大嘰嘰公子,能飛起來嗎?”
小頂拍拍大紅的屁,鼓勵道:“你,飛飛看。”
迦陵鳥生來高貴,一出生便是群妖之首,何曾過凡人奴役,只當沒聽見。
小頂捧著臉嘆了口氣:“不會飛啊,要不還是……”
“吃”字還沒出口,大紅“嘰”了一聲,就地一滾,兩短支起碩的子,開始力撲騰翅膀。
奈何構造天生有缺陷,翅膀太短,離地三尺便無以為繼,眼看著要落下來。
然而許是被吃掉的恐懼催生了潛能,只聽“轟”一聲巨響,尾忽然噴出火來,鉆天猴似地躥上了天,拖出長長一條濃煙。
眾人:“……”
翌日,小頂高高興興騎著的新生兒去上學堂。
涵虛館的學子們只聽外面傳來一陣“轟隆隆”的巨響,紛紛跑出去,抬頭一看,只見蕭頂騎著一只通赤金、威風凜凜的。
屁冒火,轟鳴不止,別提有多威風了。
弟子中多的是有錢人家的爺,便有人不服氣,質問云中子:“掌門,門規不是說弟子在門派中一律只能騎紙鶴嗎?為何蕭頂能騎別的坐騎?”又不差錢,誰不想整個拉風點的坐騎。
云中子如實答道:“蕭小友騎的就是紙鶴。”
嚴格來說,這只兩百斤還帶噴火冒煙的玩意兒,按種來分,還真就是只紙鶴。
眾弟子:“……”
小頂新得了個兒子,著實新鮮了幾日。
每天騎著大紅早出晚歸,回去還要給他做飯——所謂做飯就是把紙撕小片,再玉米粒大小。
大嘰嘰沒事就在院子里跑圈,得多吃點補補。
此外還得教他規矩,雖說還是個孩子,但也不能不知禮數,張就罵人。
一忙起來,倒把給金道長做爐鼎的事拋到了腦后。
約莫過了四五日,小頂忽然想起這樁事來,便即去提醒連山君:“蛋已經,生出來了。”
蘇毓佯裝聽不出的言外之意,掀起眼皮,瞥了一眼在院子里努力做俯臥撐的大紅:“嗯,看到了。”
小頂狐疑地看著他,懷疑他又要翻臉不認賬,蹙起雙眉道:“你答應過,生完孩子,把我給,金道長。”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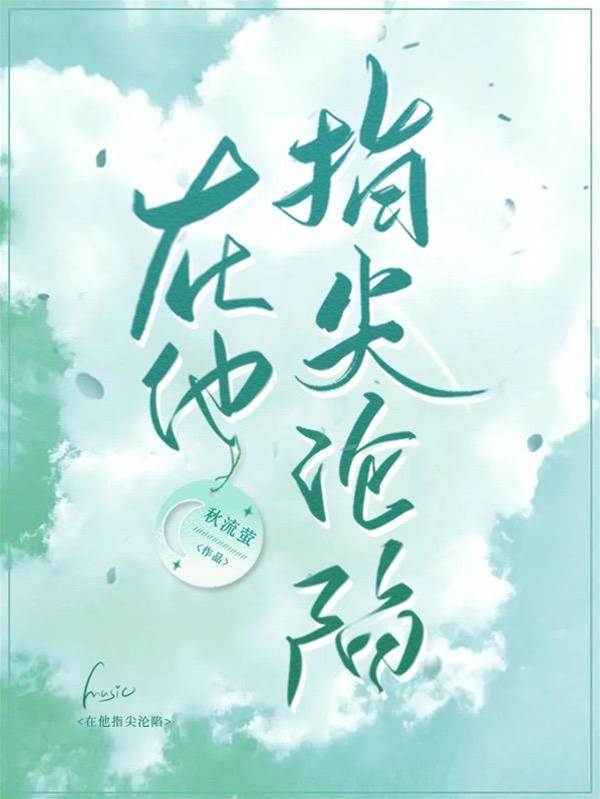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18 22009 -
完結103 章

烈吻私欲
【撩蠱?強占有欲?久別重逢?雙潔甜欲?救贖】清冷旗袍美人??瘋批西裝暴徒從小循規蹈矩的秦桑做過兩件瘋狂的事。一是分手前主動且激烈的與盛煜忘我纏歡。二是名校畢業的她放棄了體麵高薪的工作在一座小城開了一家小花店。她喜歡穿旗袍,成了那條街遠近聞名的旗袍美人。秦桑消失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在她家門前等了一天一夜的盛煜快要被大雪淹沒,寒冷刺骨。後來酒吧重逢,他誤以為她做了陪酒,心疼到骨子裏卻語調冰冷無情:“陪酒?包Y麼?多少Q一晚?”滿目可憐泛紅的秦桑望著多年未見已然冰塵冷漠的男人,委屈又倔強:“盛總平時給人多少錢就給我多少好了。”“平時?嗬~沒包過。”盛煜麵無表情隻嗓音犯冷“我嫌髒”“那盛總不嫌我髒?”“嫌你?你哪我沒親過?”————圈裏人都說港城盛家太子爺瘋批如魔,殘暴冷戾,唯獨對情愛禁如佛子,仿若不喜女人,卻又會在每年的情人節重金拍下一權獨一無二的鑽戒。沒有人知道是送給誰,直到一段視頻流出:透明的升降電梯裏,那個殘暴冷戾的男人滿身冷冽氣焰的將一性感妖嬈的美人按在懷裏吻得如瘋如魔……————人海茫茫,我隻愛過你一人,隻愛你一人。
22.1萬字8 21940 -
完結190 章

鬢邊待詔
曾名動洛陽的清貴公子裴望初,一朝淪爲惡名昭彰的嘉寧公主的待詔。 謝及音待他不好,他像個奴才一樣,每天給她挽髮梳頭,跪地穿鞋,爲她端水盥洗。卻仍動輒遭到懲罰與打罵。 後來他被折磨死了,草蓆一卷扔進亂葬崗。再後來,他死裏逃生,東山再起,率軍踏破洛陽城,自立爲帝。 衆人都以爲他恨毒了謝及音,要報復她曾經的折辱。可是裴望初在空蕩蕩的公主府裏掘地三尺,因爲找不到她快要急瘋了。 誰都不知道這座闃寂的公主府裏曾經藏了多少祕密,聲名狼藉的公主殿下和她危在旦夕的待詔公子在這裏相愛,爲了保住他,他的殿下不惜自毀名節,步步行於風口浪尖。 如今他坐擁宮闕千重、山河萬里,夜深難寐之際,裴望初望着空蕩蕩的雙手,懷念謝及音落進他懷裏的滿頭長髮。 小劇場: 裴望初下朝時,謝及音剛剛睡醒。 他熟練地從婢女手中接過水盆和帕子,輕車熟路地服侍謝及音起床洗漱,屈膝跪地爲她穿好鞋襪。 “今日梳飛仙髻,戴紫玉琉璃步搖,好不好?” 年輕俊逸的帝王拾起髮梳,溫柔地爲她通發。 久居宮中服侍的老人早已見怪不怪,剛被塞進宮想要謀得聖寵的新人卻嚇了個半死。 謝及音見狀輕嘆了一口氣。 “陛下……” 微涼的手掌落在她肩頭,似提醒,又似警告。 謝及音及時改口。 “巽之,你不要嚇着別人。” 裴望初笑了,一副謙遜柔順的樣子。 “我惹殿下生氣了,殿下罰我便是。”
31.8萬字8.18 31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