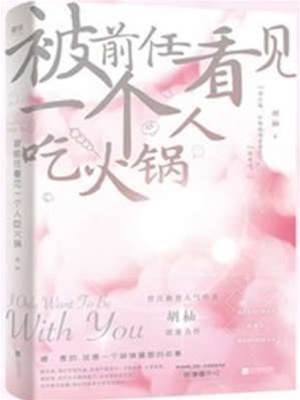《我有霸總光環》 第57章
第五十七章
林明珠實在沒想到, 本來只是吃瓜,卻因為楚楚的一句話,瞬間淪落瓜。楚彥印心生狐疑,他不快地向林明珠,斥責道:「想喝湯,你就給熬, 在這裡瞎鬧什麼!?」
楚彥印著實不明白, 難道楚楚和石田是由於一碗湯導致翻臉要打架?
林明珠抱著泰迪犬, 面對楚彥印的責怪, 在心中對惡人先告狀的楚楚素質十八連,面上卻僵笑著辯解:「我覺得是孩子們鬧著玩,可能跟湯的關係不大……」
南彥東出面做和事佬,解釋道:「楚叔叔,您別生氣, 他們是玩牌打賭, 燉湯只是彩頭。」
「是啊是啊,楚楚就是想討明珠開心,跟石田玩一局而已。」其他人附和。
林明珠:你們是拿了的錢吧?能不能別再提湯了!
林明珠簡直啞吃黃連, 有口難言, 覺得其他人都是楚楚的水軍,不然怎麼都在扯些細枝末節?
看向楚彥印,試圖辯解:「親的……」
「待會兒再跟你算帳!」楚彥印不耐道,他看著互不服氣的楚楚和石田,只覺頭疼裂, 乾脆詢問明理之人,「嘉年,你跟我解釋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張嘉年神鎮定,娓娓道來:「董事長,石先生邀請楚總打牌,楚總剛開始婉拒,讓我代上桌。前三局下來,石先生輸掉些彩頭,便有些不快,又強求楚總上桌。楚總推辭不過,僥倖贏了兩局,沒想到石先生發怒,雙方言語就有些過火,確實不是什麼大事。」
楚彥印眉頭微凝,又看向石田,問道:「是這樣麼?」
石田在威嚴的楚彥印面前不敢造次,他了,沒有出言否認,但總覺得張嘉年的闡述哪裡不對?雖然邏輯是通順的,但好像省略很多細節,明明楚楚的言辭也很挑釁?
Advertisement
黃奈菲狀似無心地笑道:「聽起來不像大事,只是彩頭有點大。」
「彩頭是什麼?」楚彥印問道。
「石田說要拿時延餐飲的份做彩頭,讓楚楚也拿出自己的份……」周圍人弱弱地說道。
楚彥印聞言,差點當場心梗塞,他覺得自己的太猛跳,完全不知道該如何理此事。如果楚楚真的拿走時延餐飲的份,兩家的就徹底破碎,拼都拼不起來了。
楚彥印後悔不已,覺得自己百一疏,就不該讓來。能一扳手擊垮南家,當然也能打牌撕石家?
楚彥印看到楚楚理直氣壯的表,更是氣不打一來,率先發怒道:「我讓你來是跟大家聚聚,你卻攪出什麼事來!?」
如果是往日的楚楚,現在必然要出言跟楚董頂撞,非跟他掰扯得天翻地覆。此時,楚楚卻難得示弱,在眾人面前似要泫然泣,委屈道:「我都說了不玩的。」
楚彥印看可憐的樣子一懵,頓時滿目茫然,他本以為會當場炸,沒料到是這種反應。
楚楚佯裝失落,繼續控訴:「別人家的小朋友都有自家份,只有我沒有,當時我就說不玩了……」
石田都有時延餐飲的份,卻沒有齊盛的份,實在太傷自尊了。
楚彥印:「……」
楚彥印:這是暗地責怪起我?
張嘉年看楚楚眼圈泛紅,眼眸中閃爍著忍的波,他竟然都有些猶豫,不知是演技真,還是真流。雖然的言辭稍有些氣人,但自始至終確實不是挑事者。楚彥印直接指責楚楚,頗有失公允。
張嘉年提議:「董事長,我覺得也該聽聽楚總的解釋。」
楚楚立刻順桿爬,悵然道:「他怎麼會聽我的話?每回都是直接罵我……」
Advertisement
眾人同地著楚楚,同時向楚彥印投去不贊同的眼神,有人勸道:「楚董,家教甚嚴沒錯,但也別把孩子太了。」
楚彥印:「……」
楚彥印覺得已經深通輿論行銷,現在都能靠外界言論,給自己父親施了。
楚彥印擺擺手,頭疼道:「份的事一筆勾銷,實在是胡鬧!」
楚楚在心裡暗「切」一聲,早料到份的事不可能有效,所以當初懶得下場。楚彥印如此重視人脈面子,怎麼可能容許做此等大逆不道之事?當時就明白,打牌贏了也不一定拿得到份。
石夫人出面調停,公正地說道:「楚董,我知道您怎麼想的。我們願賭服輸,既然石田敢把份擺上桌,我家肯定也不會賴帳。」
「大家都是朋友,又是證人,石家和時延都丟不起這個臉。」石夫人環顧一圈,擲地有聲道,「我想老石也不會出爾反爾。」
石田驚道:「媽,你怎麼能這樣,我會被爸打死的!」
「哼,現在你知道怕了?」石夫人冷笑道,「要是能讓你長個教訓,這份輸了也值!」
楚彥印為難道:「哪裡的話,您這是讓我以後,沒臉再見石董……」
石夫人的格倒是爽利,大氣道:「楚董,今天我們要是賴帳,我才是沒臉再見各位了。」
「楚楚,你過來。」石夫人朝楚楚招招手,出和煦的笑容。
楚楚看對方如此熱,一時無所適從,不過還是走了過去。石夫人拉著到桌邊,又把不不願的石田過來。石夫人看向旁邊,出聲道:「誰來擬合同?現在就辦手續吧。」
楚楚竟有種春節被長輩塞紅包的覺,連忙道:「阿姨,使不得,使不得……」
Advertisement
上這麼說,心裡想的是:謝謝阿姨,請多塞點。
石田嚇得失魂落魄,語氣中都夾雜著哭腔:「媽,你是認真的嗎?我錯了,你饒過我這回好不好?」
石夫人對他的哀求置若罔聞,冷聲道:「有所失,才能有所悟。」
楚楚和石田在石夫人的見證下,順利完份接。
【恭喜您完任務,「霸道總裁」環已加強。】
眾人看過熱鬧吃完瓜,也開始陸續告辭,到了散場的時候。楚彥印送石家一行人出門,看著端莊的石夫人和怨憤的石田,無奈道:「真沒想到會出這種事,您和時延以後有要幫忙的地方,儘管跟我說……」
楚楚可以不管不顧地收下份,楚彥印卻不能做出這種事。既然石夫人出面給了份,楚彥印作為家長,當然也要進行善後,在其他方面彌補時延。
石夫人笑道:「楚董實在不用客氣,本來就是孩子們的玩鬧。楚楚和石田年齡相差也不大,就當不打不相識,個朋友好了……」
如果只是朋友,需要上升到送份的地步麼?
楚彥印從石夫人的話中讀出其他意味,便只是客套地笑了笑。
石夫人見他不言,又婉言道:「您也別讓楚楚老忙工作,搞得連碗湯都喝不上。您要是忙,就讓來我家坐坐,我可是歡迎得很。」
「子鬧,實在怕打擾……」
「楚楚哪裡鬧,我看還行啊?」石夫人掩笑道,「聽說去泉竹軒?那還不如來我家裡呢。」
「呵呵,您客氣了。」楚彥印皮笑不笑道,他萬萬沒想到,不孝還能被人相中。
石夫人的算盤打得不錯,份落楚楚的口袋,兩家要是有聯姻,一來一去又回來了,還就一樁好姻緣。
Advertisement
楚彥印可不敢貿然答應這種事,萬一提著扳手把石家抄了,那他才真是回天無力。
屋,楚楚見其他人都離開,立刻懈怠地癱在椅子上,抖了抖手中的紙質協議。
張嘉年坐在旁邊,用沉水似的眼眸向,小聲地問道:「您剛才是真哭了麼?」
楚楚低頭檢查協議,隨口道:「當然不是,我怎麼可能會哭?」
張嘉年無言,他早該料到,楚總心如磐石,估計全是演技。
楚楚反應過來,抬頭笑道:「你以為我真哭?」
張嘉年瞟一眼,淡淡道:「我被您矇騙,又不是一兩回。」
張嘉年時常被耍得團團轉,居然已經習以為常。
「話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嘛。」楚楚不要臉地湊上來,笑嘻嘻地說道,「張總助要是實在想看,我也可以勉強出幾滴,好歹當年上過表演課。」
張嘉年:這得是鱷魚的眼淚吧。
他捕捉到新資訊,不由狐疑道:「您以前還上過表演課?是在影視院校麼?」
等等,說好的黨員修士呢?怎麼還學表演?
楚楚發覺自己得意忘形,竟一時失言。將紙質協議遞給張嘉年,不由岔開話題:「你幫我收著吧。」
張嘉年接過協議收好,不過他還是直直地向,質問道:「您沒有別的想說嗎?」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話簡直沒一句靠譜,這回難得出馬腳。
楚楚在他明澈的目下無所遁形,遲疑片刻,眨眨眼道:「張總助真好看?」
張嘉年:「……」
他頓時有種火燒似的赧意,又在的胡言語中了陣腳。
楚楚看他彆扭地側開臉,發覺此招有效,立刻欠欠地湊過去,重複道:「張總助真好看。」
張嘉年這回直接背過,他選擇對著牆壁自閉,連看都不看。
楚楚越發得意,語氣更為真摯:「張總助真好看!」
「……夠了。」他不自然地悶聲道,盡力抑過快的心跳,想要掩飾微微發紅的耳。
「不夠。」楚楚搖了搖頭,振振有詞道,「真理就該被當做標語刷在牆上!」
張嘉年:「……」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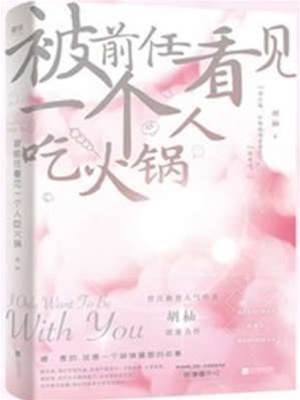
被前任看見一個人吃火鍋
【葉陽版】 葉陽想象過與前任偶遇的戲碼。 在咖啡館,在電影院,在書店。 在一切文藝的像電影情節的地方。 她優雅大方地恭維他又帥了, 然后在擦肩時慶幸, 這人怎麼如此油膩,幸好當年分了。 可生活總是不盡如人意。 他們真正遇到,是在嘈雜的火鍋店。 她油頭素面,獨自一人在吃火鍋。 而EX衣冠楚楚,紳士又得體,還帶著纖細裊娜的現任。 她想,慶幸的應該是前任。 【張虔版】 張虔當年屬于被分手,他記得前一天是他生日。 他開車送女友回學校,給她解安全帶時,女友過來親他,還在他耳邊說:“寶貝兒,生日快樂。” 那是她第一次那麼叫他。 在此之前,她只肯叫他張虔。 可第二天,她就跟他分手了。 莫名其妙到讓人生氣。 他是討厭誤會和狗血的。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讓她說清楚。 可她只說好沒意思。 他尊嚴掃地,甩門而去。 #那時候,他們年輕氣盛。把尊嚴看得比一切重要,比愛重要。那時候,他們以為散就散了,總有新的愛到來。# #閱讀指南:①生活流,慢熱,劇情淡。②微博:@胡柚HuYou ③更新時間:早八點
19.1萬字8 7230 -
完結227 章

戀愛腦暴君的白月光
“你爲什麼不對我笑了?” 想捧起她的嬌靨,細吻千萬遍。 天子忌憚謝家兵權,以郡主婚事遮掩栽贓謝家忤逆謀反,誅殺謝家滿門。 謝觀從屍身血海里爬出來,又揮兵而上,踏平皇宮飲恨。 從此再無鮮衣怒馬謝七郎,只有暴厲恣睢的新帝。 如今前朝郡主坐在輪椅上,被獻給新帝解恨。 謝觀睥着沈聆妤的腿,冷笑:“報應。” 人人都以爲她落在新帝手中必是被虐殺的下場,屬下諂媚提議:“剝了人皮給陛下做墊腳毯如何?” 謝觀掀了掀眼皮瞥過來,懶散帶笑:“你要剝皇后的人皮?” 沈聆妤對謝觀而言,是曾經的白月光,也是如今泣血的硃砂痣。 無人知曉,他曾站在陰影裏,瘋癡地愛着她。
35.1萬字8 4916 -
完結73 章

被退婚小叔寵上天
【古典嬌軟小仙女VS江南大家族長子】遇辭出生的那年,裕園的晚櫻開得極盛,花團錦簇,嬌粉欲墜。住在裕園的傅則奕,給她取了個小名,鬆月。鬆前有月,照緋櫻開。遇辭十四歲那年,父母先後去世,祠堂火燭搖曳,無人吱聲。傅則奕坐在中堂的主位上,遠遠看了她一眼,說:“跟我走吧,跟我回裕園。”後來,亭臺軒榭,錦繡裕園,江南涳濛的煙雨裏,她曾動了不該動的心思。-年齡差八歲/偽叔侄
15.2萬字8 13508 -
完結178 章

春長渡
沈支言出身於名門望族,才情卓越,樣貌出衆,十七歲那年,她嫁給了親王府的二公子薛召容。 薛召容,一個無論是樣貌還是才華都在頂尖之列的貴公子,在與沈支言訂婚以後,才知道她已經有了愛慕的白月光。 成婚那日,婚禮格外隆重,驚動了整個京城。 可是,新婚第二日,沈支言就搬去了別院中。 一年後,朝中生變,親王府被滿門抄斬。 · 那年冬天雪下的有點大,冰涼刺骨的斷頭臺上,沈支言望着薛召容,在他眼中看到了愧疚與不捨,還有讓她分辨不清的柔情。 他笑得苦澀,對她說:“支言,若有來世,別再遇到我了,對不起,是我連累了你。” 那一年,他二十二歲,她十八歲。 · 重回陵國二十六年。 那日,下着雨,薛召容跟着父親前來商議婚期。 大人們在堂中議事,沈支言和薛召容則被母親安排到了客房裏。 · 屋外的雨聲有點大,昏暗的光線下,沈支言擡眸去看他。 他長身玉立,眉目如畫,矜貴的讓人移不開眼睛。 · 他與上一世一樣,面上總是冷冷冰冰。 他低眸看她,嗓音清冷:“沈姑娘,你我的婚事,乃屬父母之命而不可違之,婚後我會住在偏房,絕不擾你清淨。” 屋外的雨聲幾乎淹沒了他的聲音。 她轉身去關窗戶,輕聲回他:“薛公子莫要擔心,我已經在與父親商量退婚,相信我們很快就能恢復自由之身。” 房間裏安靜下來,她再看他,卻在他眼中看到了複雜。 · 不久後,他們還是成婚了,她再次嫁給了他。 她以爲,他們還會與前世一樣,婚後分房而睡,互不打擾。 可是那日,他突然找來,要與她商量同房的事情。 · 她洗漱完擦着秀髮,開門請他進去,問道:“薛公子這麼晚過來可有要事?” 她依舊叫着他“薛公子”。 他心裏突然酸酸的,望着膚質雪白滿頭青絲的她,默了片刻,回道:“最近有幾個婆子總在背後議論,說你我二人不和,有和離的打算。還說……你表哥升官加爵,新府邸搬到了我們隔壁。爲了消除這些不友善言論,我覺得,我們還是別再分房睡了。” 他頓了片刻,聲音低了一些:“今晚……我想睡在你這裏。” 他說罷,掏出一盒口脂放在了桌子上。
47.3萬字8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