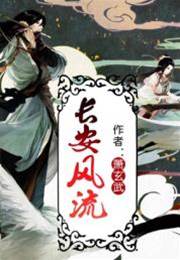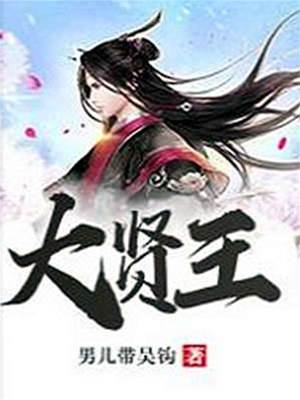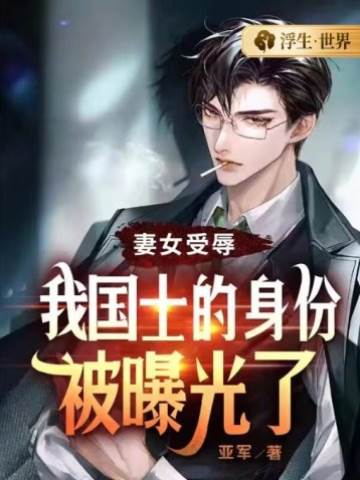《伐清》 第47節 自救
周開荒不覺得服從有什麼不對,但這次的功讓他有些迷,那就是:如果將來明軍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如果有一隊清軍利用繳獲的印信在明軍境大肆破壞怎麼辦?以往的規矩就是,一旦印信丟失就要立刻上報,以最快的速度重鑄新印並通報新的規格。以前周開荒認爲這樣理就已經足夠,但現在他親眼看到這樣是不夠的,而且是遠遠不夠的。以前沒有人這樣迅速地利用繳獲的印信發起攻擊,並且是連續不斷的攻擊。更甚者,對於一支經驗富的小分隊——比如他們現在的這種,就是沒有印信,也能利用對的瞭解給敵軍造重大的損失。
“需要有一支部隊,專門檢查印信的真假,還有兵份的真假。”周開荒提出的疑問馬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看來這些日子所有的衛士都考慮過類似的問題。
“怎麼可能知道所有將領的印信?怎麼可能到都有這種檢查印信的部隊?”
“或者說只有一支特別的部隊可以決定生死。”又有人說道。
“這更不可能了,難道這支部隊還能管到別人的家丁和親兵裡面去嗎?是不是該死難道不是由上峰說了算,反倒由這支部隊說了算麼?誰會同意?”反對者覺得這個想法太不切合實際,因爲明顯地涉及到了軍的固有權利,侵犯了“大小相制”的慣例,侵犯了傳統的封建權利。
Advertisement
鄧名有些茫然地放下筆,他約約地覺道,這些部下現在正在討論的那支特別的部隊,好像有點類似未來的憲兵部隊,而他們的討論似乎還涉及到了一些現代軍隊的制。
討論雖然熱烈,但沒有任何結果。
臨睡前鄧名算算天數,若是劉晉戈過去了,這個時候他和袁象也差不多該開始返回建昌了。
……
此時,狄三喜帶著三百士兵,千多輔兵、一些糧食和無限的悲壯離開了建昌。
昨天,狄三喜用出城搜索鄧名的行蹤爲理由,向馮雙禮告辭。後者凝視了他很久,最後艱難地點點頭:“天下沒有不散的宴會。取酒來!你我二人今日要痛飲一番。”
好不容易,狄三喜才讓馮雙禮相信他不是要畏罪潛逃。是的,狄三喜不願意被殺掉,但他也不想做一條喪家之犬;狄三喜更不會去吳三桂那裡,沒有了奉獻建昌這個功勞,他去了也不會到禮遇,說不定還會被遷怒,命運未必就比逃亡荒郊強。
雖然解釋了很久,但今天出城前,馮雙禮和一些往日好的同僚還是送來了一些金銀——狄三喜怒不可遏:我不是要逃亡,不需要這些盤纏。
Advertisement
當發現狄三喜出城時沒帶家眷,軍們和士兵們的臉上出現了掩飾不住的驚訝之。狄三喜按下心中的煩躁,沒有去和他們計較,因爲這麼想的人太多了。幾個忠心耿耿的衛士聽狄三喜說要出發去找鄧名後,首先提出的要求是多給點時間,讓他們能搬運家小一起離開建昌。
至於那些點頭之,此刻全都站得遠遠的,看到他們躲躲閃閃的樣子,狄三喜心中生出了一個猜測:或許大家都暗暗慶幸狄三喜出走呢,而且盼著他再不要回來,這樣就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他的上,不但不用擔心他魚死網破到奉節去胡說八道,而且放狄三喜一馬還有助於同謀們獲得良心上的安。
“去東川!”出城後,狄三喜看了看忠心耿耿的家丁和親兵們,說出了此行真實的目的地。
狄三喜猜測鄧名不會就此放棄建昌返回奉節,但即便鄧名真的沒有如他所想的去東川,那狄三喜也要拚上命去東川一搏——自己赤膊上陣去搞一通破壞,來挽回自己的形象:我不是大白臉而是忠臣;我不是白鼻樑而是有勇有謀的良將!
Advertisement
親衛們都默默地點頭,一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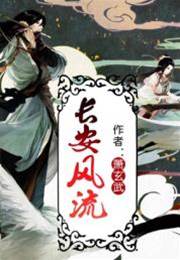
長安風流
貞觀大唐,江山如畫;長安風流,美人傾城。 妖孽與英雄相惜,才子共佳人起舞。 香閨羅帳,金戈鐵馬,聞琵琶驚弦寂動九天。 …… 這其實是一個,哥拐攜整個時代私奔的故事。
207萬字8 23479 -
連載25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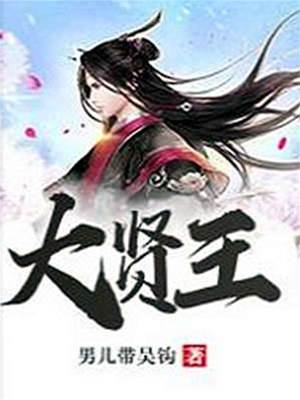
大賢王
景曆115年,天下紛亂,三國鼎立。昏迷三年了的壽王世子葉灼在這一天睜開了眼睛...葉灼本隻想安安靜靜的當一條鹹魚,做一個聲色犬馬的紈絝,可奈何,人太優秀了,到哪裡都會發光。且看葉灼如何在這亂世之中,闖出一條隻屬於他的賢王之路!
476.6萬字8.18 70497 -
完結1544 章

抗戰之重整河山
當山河破碎之時,總有中華健兒捨身忘死。 有膽敢覬覦中原大地之鼠輩者,必將頭破血流,血債血償。 山河陸沉之際,江東魂穿抗日戰場, 從淞滬會戰開始,帶領一個個中華熱血男兒, 殺倭寇,復河山。 我們的,必不讓人奪了去。 屬於我們的,也將取回來。 侵中華者,必懲之!
386.2萬字8 25328 -
完結85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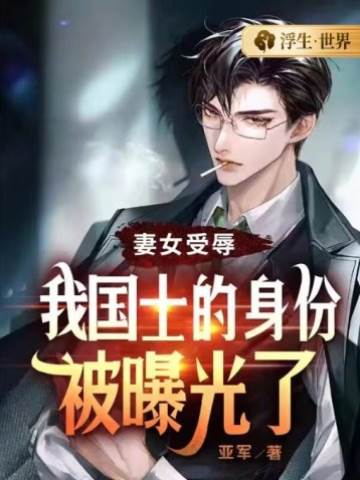
妻女受辱,我國士的身份被曝光了
隱名埋姓在大漠搞科研卻接到了女兒的電話……無雙國士從大漠回歸這一刻,他勢必要攪動風雲!
154萬字8.18 147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