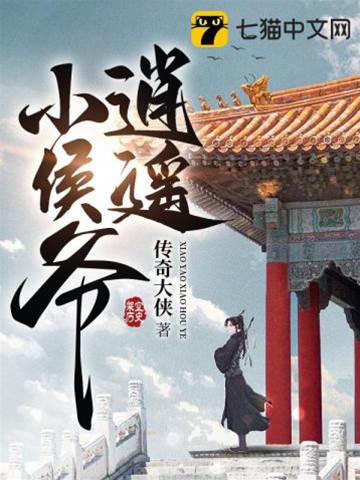《數風流人物》 乙字卷 第一百三十二節 諸般心思,卻上心頭(第一更求月票!)
這二十日恐怕對所有學子們都是最難熬的二十日。
春秋兩闈這種考試的確變數太大,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
甚至可能因爲你寫的卷子卷面不佳,或者字跡不清晰,都可能直接被黜落,同樣,在經義策論中,你的文章如果不合房師的口味,也有可能被廢置,這種況數不勝數。
對馮紫英來說,也不例外。
雖然範景文很肯定的表示,在這一科的春闈中,自己應該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如果這都沒能過的話,那就是天命了,但馮紫英同樣也清楚,這種可能的確存在。
很多房師對經義十分看重,雖然從元熙三十五年之後,時政策論的分量日益上升,但是畢竟裁決權在房師們手中,如果他們認爲自己的經義水準太差,給了一個非常糟糕的判語,那麼也是可能直接被黜落的。
關鍵就在於這判卷的房師們對經義文卷的審覈寬嚴程度。
這就真的不是哪一個人能控制的了,遇上寬鬆的,他只要覺得過得去,都可以給你判一個不錯的判語,遇上嚴格的,你在經義論述中稍微和聖人之言不符,他都可能要讓你失去這樣一個機會。
******
黛玉也在一起牀之後和紫鵑探討著這個問題。
這一年,對於黛玉來說也是難熬的一年。
府裡邊多了一個寶姐姐,嫺雅大氣,待人接都是極好的,而且人也大方溫和,這也使得府裡邊就有些閒言碎語出來了。
兩個表小姐,一個是姑表小姐,一個是姨表小姐,都相當於是寄居在賈家,但是子卻各異。
黛玉本來就不出門,加上面冷利,免不了要得罪一些婆子僕僮。
Advertisement
而丫鬟們則都是慣於趨炎附勢的,林姑娘對寶二爺一直沒有多好臉,也使得很多丫鬟們覺得這位林姑娘過於驕矜倨傲,慢慢的就免不了要在背後說些閒話了。
也幸虧得紫鵑是府裡的老人了,和鴛鴦、平兒、襲人等人關係都一直不錯,加上原來也是在老祖宗邊兒上呆過的,多也還是有些面子,所以這形纔沒有過於嚴重。
但下人們對薛家姑娘的口稱讚卻是發自心的,這位薛家姑娘,見人先帶笑容,而且從無惡語冷臉,便是有些爲難事,也要儘可能的替人考慮到,端的是個周到人。
這兩相對比之下,大家心裡便自然也就有了一個掂量,雖說像黛玉日常接比較多的二嫂子、探丫頭、二姐姐都無甚影響,但是像其他一些人多也就還是有些看法了。
黛玉不是不到這種變化,但是卻懶得去多理睬,本來也就沒有多道,何必要去刻意討好誰,或者向誰去解釋個什麼?
怎麼想怎麼想,信就去信好了,大不了日後打道甚至不打道。
這就是的風格。
便是紫鵑也改變不了自家小姐這方面的子,頂多也就是幫圓轉維護一番,以免把很多關係弄得太僵,比如像後房,黛玉胃口本也不好,很多時候還要有求於後房;再比如一些送花送脂的,總歸要打道,自然也要想辦法避免被人家針對。
“馮大爺今兒個也不過才虛歲十五,這大周朝好像沒有聽說過十五歲的舉人吧?珠大爺當年十五歲也只是考了個秀才,就那樣弄得闔府上下都是張燈結綵,很是歡鬧慶賀了一番,若是馮大爺考中舉人,只怕就要舉國皆驚了。”
Advertisement
紫鵑先替馮紫英把臺階找好,這邊也算是替自家小姐打個圓場,別到傳出去馮大爺能考過,最終馮大爺卻又未過,弄得大家面上尷尬。
若是從小姐裡傳出去,只怕就有人要專門來就此話懟小姐了。
“紫鵑,那也不一定,我聽說今科北直隸名額不,馮大哥這兩年也一直苦讀,今年年後就再也沒有出來過,一門心思要考過,這邊努力,怕是過得了的。”
對馮大哥的前程,林黛玉一直是十分關注的,爲此這半年裡也是多有了解,只不過一個人在府裡邊,能打聽的渠道有限,也就只能憑著自己的想象去琢磨。
“小姐說過得了,那便過得了吧。”紫鵑笑著應和了一句。
這等問題只要一扯起來,只怕小姐又要爭個高下才罷休,換了其他話題都好說,小姐多半不會在意,唯獨這個話題,那是不肯退讓的。
似乎是覺出了紫鵑語氣裡的某種退讓,嗯,還有點兒揶揄的味道,黛玉臉一紅,瞪著紫鵑:“紫鵑,你這口氣是什麼意思?什麼我說過得了,就過得了?我是據馮大哥這麼努力判斷的,你看尋常事馮大哥哪有那麼努力過,這樣的形有過麼?”
紫鵑只得正道:“小姐,婢子不懂這個,只能是小姐怎麼說就怎麼了,想那馮大爺如此能耐,不知道是否瞭解小姐在替他默默的祝福呢?”
這一下子黛玉臉刷的一下是真紅了,拿起手中的汗巾子就要打紫鵑,卻被紫鵑格格笑著躲過,“小姐,婢子說錯了。”
藉著機會,紫鵑出去替黛玉泡茶,回來時,卻見那黛玉癡癡的著窗外,半晌不,顯然是這份心思早已經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心中也是暗自嘆息,這馮大爺若是辜負了小姐這般心意,那就是罪該萬死。
Advertisement
看看小姐的手,爲了馮大爺,生生的繡出了一個香囊來,這普天下再無一個男人能讓小姐這般了。
********
同一時刻。
薛蟠一搖三晃的進了院子,卻見這屋裡沒甚人氣。
母親怕是去了姨母那邊,這梨香院哪樣都好,唯獨就是人氣不足了一點兒,畢竟不是自家屋裡,這院子也小了點兒,啥擺設也只能由著別人來將就。
再看看自家邊,連個像樣的使喚丫頭都沒有,再聯想到那越發標緻俊俏的香菱,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那金陵那邊怕也是事已經該了結了,舅舅似乎這一年裡也未曾提起過這事了,或許自己可以向妹妹那邊把香菱重新討要回來?
但想到舅舅那張冷厲狠的臉,薛蟠有下意識搖了搖頭,恐怕還得要緩緩,總得要等到金陵那邊有個準信兒,方能作數。
想著這些事,薛蟠便徑直步自己妹妹那邊的偏院,“妹妹在麼?”
“兄長什麼事?”薛寶釵的聲音永遠是般清泠溫潤的,漫步走到門前,卻見自己兄長有些不自在,再一看,那香菱也看到了兄長,當是還有些忌諱和尷尬。
這一年多裡,香菱跟了自己,便有出門,儘量避免與兄長面,自家兄長雖然是個渾人,但是答應了舅舅的事卻也十分守諾,自己這邊院裡便是半年都難得踏足一次。
“也沒見著母親,怕是去了姨母那邊,我今日看那街上,一干儒生呼朋引伴,縱笑談論,不知是何節日,讓這些酸丁如此興?”
薛蟠目不斜視,只看著自己妹妹,那香菱也早就躲屋裡,只有鶯兒笑著和妹妹迎了出來。
“兄長有所不如,昨日秋闈大比便算是考完了,這些學生們怕也是要輕鬆愜意一番吧。”薛寶釵微笑著向兄長解釋。
Advertisement
“哦?難怪。”薛蟠恍然大悟,臉上哂笑之意甚濃,“難怪今日裡我看到寶兄弟懨懨的,只怕也是聯想到了此事,下科怕是他也要去參加秋闈了?”
寶釵何等人,如何能聽不出自家兄長語氣來的揶揄調侃味道,瞪了兄長一眼,“兄長,這等話萬不可在外邊說,否則被府裡其他人聽了去,定要惹出是非來。寶兄弟現在年齡尚小,下科也未必就要去考,多讀幾年書未必就是壞事。”
“妹妹,話不是這麼說吧?這讀書不就是爲了去考試麼?我聽聞這府裡都在說那馮家大郎今科便是要去考的,馮家大郎也不過就是大你月份,那下一科寶玉當是比現在的馮家大郎年齡更大,爲何卻不能去考?”
薛蟠在其他事上或許就過了,唯獨在寶玉讀書的事上卻是格外清醒,“莫不是怕考不起,丟了臉?也不至於如此纔對。”
寶釵臉紅了紅,見兄長一副較真模樣,只得小聲解釋:“兄長有所不知,這要參加秋闈也不是人人都能參加的,須得要先考過秀才,或者就得要取得監生資格,否則是不能去考的,下科秋闈,也還要看寶兄弟那時候能不能取得這樣的資格,這等事兄長莫要去多問,免得寶兄弟多心。”
薛蟠眨眨眼睛,似乎是明白了過來,點點頭:“原來如此,若是寶玉考不過秀才,那邊去弄個那勞什子監生資格便是,那又有什麼難,總歸不過是多使些銀子便能解決。”
寶釵未曾想到在這等事自家兄長居然還如此看得穿,這要其他辦法取得不了監生資格,倒也的確可以用捐監來拿到監生資格。
只不過捐監的名義就實在太難聽了,而且這大周百年幾十科裡,還從未聽聞過有捐監考中舉人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36 章

大唐之攤牌了朕真不是你爹
李二陛下出宮遇刺被救,救命恩人李易歡張口就叫:“爹?”見識了“仙器”、紅薯以后,李二陛下決定將錯就錯。魏征、房謀杜斷、長孫無忌以及程咬金等人,都以為陛下多了一個私生子,這皇位繼承人,以后到底是誰?終于,李二陛下忍不住了,找到兒子攤牌:“朕真不是你爹!”李易歡:“我還不是你兒子呢!”
126.3萬字8 10209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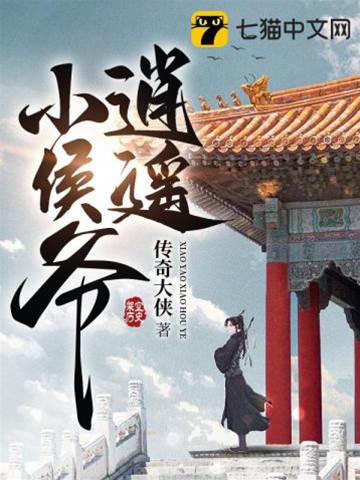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8890 -
完結444 章

混在女帝身邊的假太監
一覺醒來,發現身在皇宮凈身房,正被一個老太監手拿割刀凈身是什麼體驗?徐忠萬萬沒想到,自己只是一夜宿醉,醒來后竟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還差點成為了太監,好在凈身時發生了點意外,讓他幸運逃過一劫。從此徐忠以一個假太監身份,混跡在女帝身邊,出謀劃策…
91.7萬字8 21123 -
完結254 章
三國:截胡劉備妻,我乃祖龍血脈
祖龍血脈贏武,三千兵馬起家,奪徐州,吊打劉備和呂布! 天下諸侯,盡皆震驚! “劉備、曹操、孫權,世家之患乃是天下大亂之本!” “你們沒有能力,也沒有魄力將世家門閥根除!” “讓我贏武來吧,以戰功論賞,恢復我大秦制度,才能讓天下百姓真正當家做主!” 贏武俯視江山,立下宏願。 一段可歌可泣的大秦重造之戰,正式拉開序幕......
44.5萬字8 87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