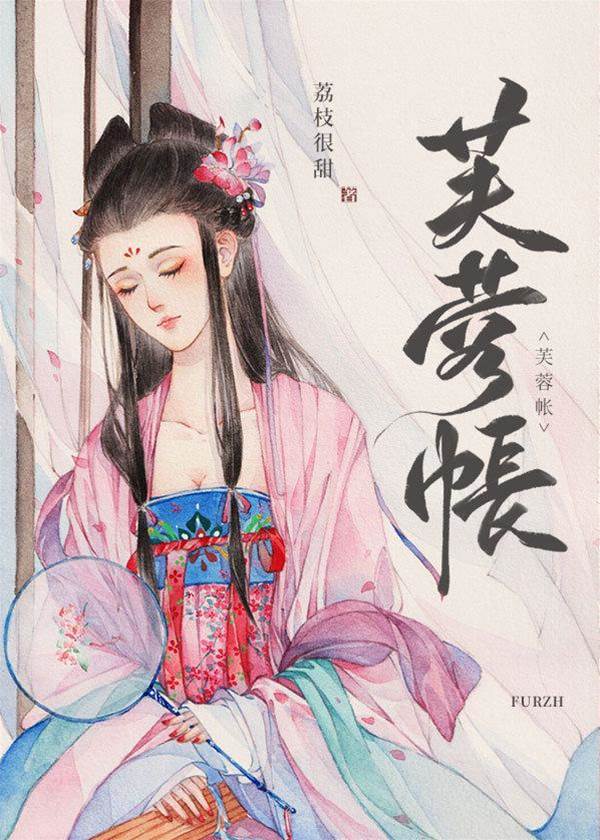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催妝》 第四十九章 小畫
飯菜端上桌,宴輕看著淩畫,有點兒不順眼。
他臉不好地對找茬,“誰讓你進我室的?”
男人的室,是隨便進的嗎?
淩畫頓了一下,“昨兒你換我給你做的新裳,用你屋子裏的鏡子對照,我也順便進去看了看。”
特意強調,“你的房間真沒什麽好看的,就是一張床,一張桌子,一麵鏡子而已。”
“沒什麽好看的,是你進去看的理由嗎?”宴輕手臂著傷,沒法雙手抱,便用一隻胳膊搭在桌子上,手敲了一下桌麵,萬分嫌棄,“你是個孩子,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淩畫眨眨眼睛,“知道。”
有點兒委屈,又有點兒無辜,自我辯解,“可是我又沒進別的男人的室,隻是進了你的室而已。”
“你的意思是,未婚夫的室,就可以隨便進?”宴輕挑眉。
淩畫直覺這裏有坑,不吭聲。
果然,宴輕挖坑,“秦桓的室,你也進過?”
“沒。”淩畫立即搖頭,“他的室,我還真不進。”
宴輕瞇起眼睛,“那誰的室你進?你都進過誰的室?”
淩畫有點兒應對不來,“隻進過你的。”
保證,“真的,七歲起,我連我哥哥們的室都不進了。”
宴輕立即說,“你以後也不準進我的室。”
淩畫不答應,“不行。”
不止想進他的室,還想上他的床呢。
宴輕冷下臉,“你在打什麽主意?我告訴你,我娶你,就是娶你而已,你給我想別的多餘的。”
淩畫佯裝不懂,“我想什麽別的多餘的?我不太懂,要不你說明白點兒?”
宴輕一噎,“你怎麽就不懂!”
他又不是瞎子,剛剛的眼神,他看的分明,那裏麵全是心思。
淩畫決定不跟他,現在說什麽也不管用,房花燭之夜再說這個才是正對日子,於是,趴在桌子上,可憐兮兮地說,“我了,咱倆能先吃飯嗎?”
Advertisement
宴輕也了,胳膊了一下,撤離桌麵,“吃吧!”
淩畫立即坐起。
昨兒還用宴輕伺候的給夾菜,今兒來晚了,讓他著肚子午睡,自然是理虧的,哪怕他一副明顯就找你茬了的神,也不敢再作妖,乖乖地拿起筷子,低著頭吃著。
這一頓飯,吃的有點兒安靜。
吃飽喝足,宴輕依舊不忘找茬,“你說,你想幹什麽?”
淩畫很認真地提醒他,“你可以去午睡了。”
宴輕涼涼地看著,“你別以為我好糊弄。”
淩畫頭疼,的確是不好糊弄的,但若是說了,怕將他嚇著,立馬衝去皇宮把婚給毀了。
“嗯?你倒是說啊?”宴輕不依不饒。
淩畫深吸一口氣,斟酌了一會兒,委婉地問他,“你知道嫁娶的意思嗎?”
宴輕哼了一聲。
誰不知道嫁娶?不知道的是傻瓜,他看起來很傻嗎?
淩畫看他一臉“你在說廢話嗎?”的鄙視神,忽然豁出去了,給他解釋,“嫁,是子出嫁,娶,是男子娶妻,嫁娶,是結兩姓之好,何為兩姓?是結發為夫妻,是之相合,是同床共枕,是相擁夢,對男子來說,求的是妻賢子孝,對子來說,夫唱婦隨。”
宴輕一臉我不懂,“你說的都是些什麽東西?”
淩畫:“……”
服氣了,笑瞇瞇地看著他,“不怎麽,我的意思是,以咱們如今的關係,我進你室,真沒什麽可大驚小怪的,你若是不同意,我不再進就是了。”
可以保證,大婚之前,都不進。
不等他繼續找茬,轉移話題,“你救不救秦桓?他如今在我手裏,我琢磨著,他實在太可恨了,打算好好折磨他,你若是救他,我看在你的麵子上,就饒了他。”
Advertisement
“不救。”宴輕果然被帶偏了,“你隨便折磨。”
那個家夥,坑了他,還想過好日子?沒門!
淩畫就知道宴輕的良心沒了憫心草,對秦桓就不顯了,點頭,“你不救最好,否則我都沒法找他撒氣了。”
“你打算怎麽找他撒氣?”宴輕還是想了解一下的。
“讓他讀書?跟我四哥一起考科舉?他不是不讀書嗎?我就押著他讀,讀不好,就他,讀好了,正好也能幫我對付蕭澤。”
宴輕覺得好,給予讚賞,“對,就這樣,再把他的酒戒了,讓他以後不準再禍害人。”
淩畫點頭,“嗯。”
雖然覺得跟秦桓喝醉了沒多大關係,那日主要是的憫心草的作用,宴輕自己喝醉了,不過這也不妨礙答應他。
宴輕心裏舒服了,秦桓苦折磨,他就渾舒暢。
端趁機端來藥碗,“小侯爺,喝藥。”
哎,如今一天三頓藥,真真是最折磨人的時候,他幾乎是掰著手指頭數著天數盼著小侯爺的傷趕養好。
宴輕看了一眼藥碗,滿眼嫌棄。
淩畫出一塊糖,在他眼前了一下,然後剝開糖紙,將糖扔進他的藥碗裏。
宴輕等著那塊糖化了,才慢慢地端起藥碗,著鼻子,咕咚咕咚一口氣喝了。
喝完,他漱口後,依舊覺得滿苦味,盯著淩畫的手。
淩畫意會,又拿出了一塊,剝開糖紙,遞到他邊。
宴輕張吃了,頓時一的甜味,驅散了滿的苦味,他看淩畫也順眼了,對問,“你要不要去看看汗寶馬?它今天又被秦桓他們看了半天。”
淩畫搖頭,“不去了,我給你的裳繡花紋。”
主要是,大熱的天,走路跟著他去馬圈,腳還沒站穩,怕忍不住喊兩聲“輕畫”,他再不高興將他趕回來。
Advertisement
畢竟,沒嫁給他之前,未婚妻不是妻,還是得夾著尾做人。
“真不去?”
“不去。”
“行吧,我自己去。”宴輕不怕熱,溜溜達達散著步去了馬圈。
淩畫拿出金線,拿出昨天的裳,將裳鋪開在桌子上,用炭筆在裳上畫出祥雲紋,然後,想了想,又在擺的大麵積畫了一連串的紫葡萄花樣,之後,落筆,滿意的看了看,開始拿了針穿了繡線,沿著畫出的樣子繡。
宴輕在馬圈裏跟汗寶馬待了一會兒,又將它放出馬圈跟在他後遛園子。
汗寶馬熱的渾直冒汗,宴輕看的十分欣喜,與它說話,“你有點兒瘦,再點兒就好看了。”
汗寶馬踢踢蹄子,不太願地頂著大太跟在宴輕後遛彎。
它覺得他這個新主子似乎腦子不太好,有點兒病,不是大半夜在馬圈裏跟它聊天不讓它睡覺困的它睜不開眼睛,就是大白天頂著炎炎烈日烤的馬都快了的日頭下散步遛彎。
偏偏他沒有毫自覺,還覺得這樣很正常。
“走,帶你認識認識小鸚去。”宴輕遛夠了,轉向後抱廈,去逗頭鸚鵡。
汗寶馬屁後麵跟著他,想著總算是能去涼快的地方了。
頭鸚鵡這兩日心很好,不用被宴輕著學唱曲,它幾乎自己嗨翻天,宴輕來時,它依舊撲棱著翅膀自嗨著,聽到宴輕的腳步,它小子一僵,瞬間收了翅膀,趴在籠子裏裝死。
宴輕敲敲鳥籠子,鳥籠子晃個不停,那頭鸚鵡愣是很有毅力地一不。
宴輕氣笑了,“幾天不訓你,長本事了是不是?”
他對外喊,“端,把它給我拿廚房去燉了。”
端自然不會。
頭鸚鵡一下子炸了,連忙爬起來,開始給宴輕唱歌,婉轉的小調,很好聽,新學的。
宴輕滿意,側開子,指著汗寶馬,“這是……它……小畫,你認識一下。”
他把自己那個輕字輕而易舉的減掉了。
汗寶馬向前走了一步,盯著裏麵唱歌的小東西,忽然覺得,它比自己可憐,至,他能被放出馬圈出來遛彎,而它卻隻能被關在籠子裏唱歌。那籠子就那麽大一點兒,還沒它的腦袋大。
它終於不哀怨了,用腦袋蹭了蹭鳥籠子,跟它打招呼。
頭鸚鵡不知是從它的馬眼裏看懂了什麽,還是本語言互通,隻見它唱著唱著大翻白眼,然後,氣暈了過去。
------題外話------
今天月票雙倍,已到月底了,求個月票,謝謝大家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19 章
腹黑世子妃日常
一朝穿越,腹黑狡詐的她竟成身中寒毒的病弱千金,未婚夫唯利是圖,將她貶為賤妾,她冷冷一笑,勇退婚,甩渣男,嫁世子,亮瞎了滿朝文武的眼。 不過,世子,說好的隻是合作算計人,你怎麼假戲真做了?喂喂,別說話不算話啊。
39.1萬字7.75 70010 -
完結652 章

重生之嫡女毒妃
枕邊之人背叛,身邊之人捅刀,她的一生,皆是陰謀算計。 一朝重生,她仰天狂笑! 前世欺我辱我害我之人,這一世,我顧蘭若必將你們狠狠踩在腳下,絕不重蹈覆轍! 什麼,傳言她囂張跋扈,目中無人,琴棋書畫,樣樣都瞎?呸! 待她一身紅衣驚艷世人之時,世人皆嘆,「謠言可謂啊」 這一世,仇人的命,要取的! 夫君的大腿,要抱的! 等等,她只是想抱個大腿啊喂,夫君你別過來!
113.7萬字8 25279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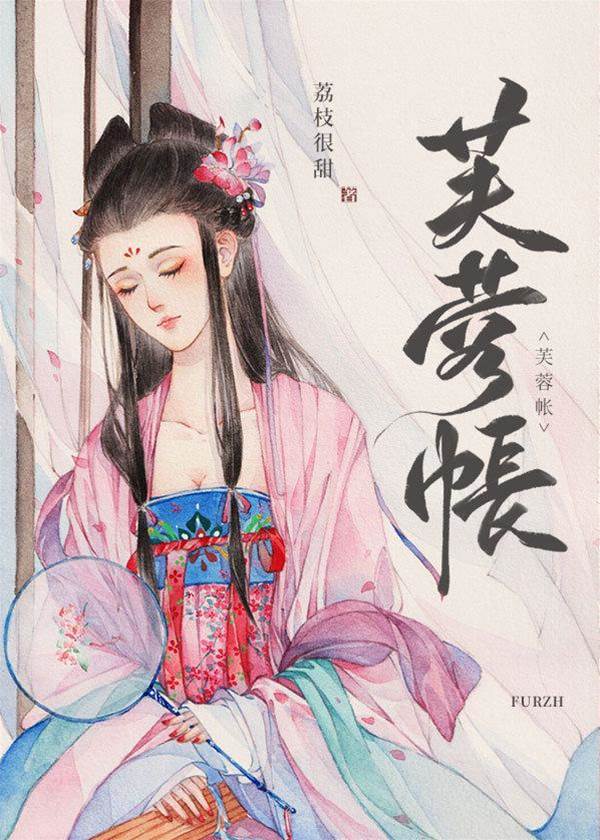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626 章

妃你莫屬:王妃,請低調
作為軍事大學的高材生,安汐無比嫌棄自己那個四肢不勤,白長一張好皮囊的弟弟安毅。可一朝不慎穿越,那傻弟弟竟然翻身做了王爺,而她卻成了那位王爺的貼身侍女;自小建立的權威受到挑戰,安汐決定重振威信。所以在諾大的王府內經常便可見一個嬌俏的侍女,提著掃帚追著他們那英明神武的王爺,四處逃竄,而王爺卻又對那侍女百般偏袒。就在這時男主大人從天而降,安汐看著躲在男主身后的傻弟弟,氣不打一處來。某男“汐兒,你怎麼能以下犯上?”安汐“我這是家務事。”某男頓時臉一沉“你和他是家務事,那和我是什麼?”安汐“……我們也是家務事。”
56.6萬字8 483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