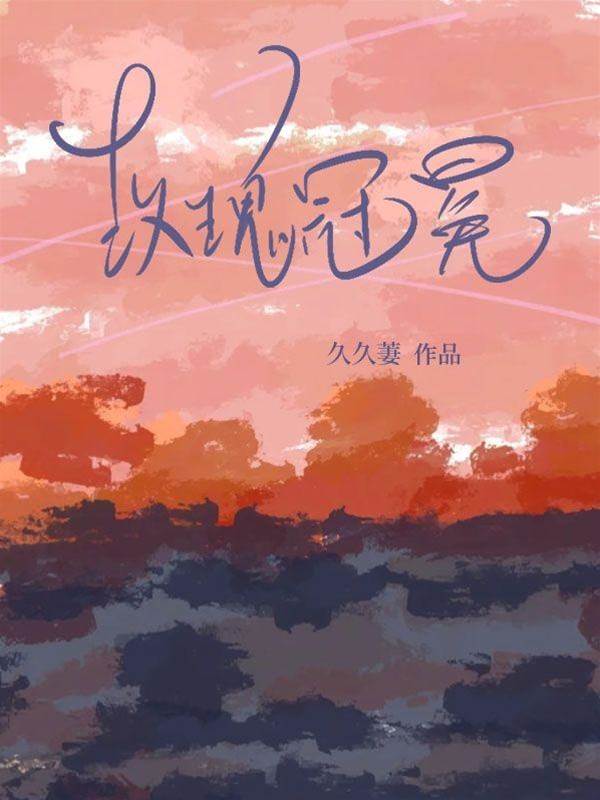《你說南境有星辰》 Chapter 42 傳遞信息
拿嬸當即提議送點漂亮貴重的花,歡雖然不懂小伊的用意,還是表示自己是連多都能養死的人,滿天星這種直接能做幹花的品種更適合自己。
小伊像是要避嫌,剪花都是拿嬸的手,隻是最後說花枝太散不好抱,用膠帶粘了一下,放進了一個方形的花瓶裏,自然膠帶和花瓶也是別人去取的。
“老師,我隨便綁了一下,花型不好,你回去可以調整一下次序再一下。”
站在花房門口,沒有送客出去的意思,歡就這樣懵懵懂懂地跟著抱了一大瓶滿天星的拿嬸離開了。
王家的後院顯然是有專人設計打理過的,奇石活溪,鬆竹蔭翳,盛夏之際依然日涼風清,別有一番幽靜。拿嬸帶著歡穿過蜿蜒小徑,也不知是不是小伊的循規蹈矩讓很滿意,心大好,熱地給因為一無所獲而失落的歡介紹起了院中木石,還手摘了枝酸杷遞來。
“老師,你放心吃,我們院子裏種的果樹都是沒打過農藥……”
拿嬸像是被誰掐住了嚨,聲音消失了一瞬,歡下意識順著的視線看過去,隻見蘿薜垂簾的深匆匆走過了一個戴著黑口罩的男人,手中拿了一個方形紙袋,正微佝僂著腰往花房方向去。
雖然拿嬸立刻又笑著轉過給歡說起了話,敦實的軀卻有意無意擋住了男人走去的方向,不過視力極好的歡在看過去的那一剎,恰好對上了男人沉的雙眼,還看到他口罩上沿一顆搶眼的黑痣。
也因為那顆在網上常被吹捧的所謂淚痣,歡頃刻間把口罩男的眼睛和案卷裏孟東勒的照片對上了,忍不住長腦袋追看過去想確認,拿嬸把滿天星高高地塞到了的手裏,一大蓬星星點點的小白花完全遮住了的眼睛。
Advertisement
“老師,你看什麽呢?”
歡回神,對上了拿嬸皮笑不笑的臉,搖擺的樹枝在臉上投下了變幻的暗影,顯得打量的目越發瘮人,歡生出了猶如小知危險的本能,幹脆大方地指了過去。
“剛才那人戴著口罩怪怪的,小伊一個人在花房呢,要不要去看一眼?”
拿嬸探究的意味不減,隨口答道:“那是家裏的花匠,因為臉上嚴重過敏怕嚇到人才戴的口罩。”
“哦,那我們走吧,我哥的司機還在外麵等著呢。”
率先往外走去,卻覺拿嬸森冷的目如附骨之疽盯在後背,盯得汗一豎了起來。
“老師,還有酒沒拿,米酒是王總找老師傅按古方釀的,外麵輕易喝不著。”
拿嬸手按在肩膀上,力道很,卻毫掙不了,歡的鼻尖冒出了汗珠,想起蘇睿的叮囑,腳下一崴直接跌坐在地,手中的花瓶也應聲而碎,抱著腳踝哼唧起來。
“老師,你沒事吧?”
拿嬸的手才到腳踝,就尖兩嗓子,大聲起來。
拿嬸當即提議送點漂亮貴重的花,歡雖然不懂小伊的用意,還是表示自己是連多都能養死的人,滿天星這種直接能做幹花的品種更適合自己。
小伊像是要避嫌,剪花都是拿嬸的手,隻是最後說花枝太散不好抱,用膠帶粘了一下,放進了一個方形的花瓶裏,自然膠帶和花瓶也是別人去取的。
“老師,我隨便綁了一下,花型不好,你回去可以調整一下次序再一下。”
站在花房門口,沒有送客出去的意思,歡就這樣懵懵懂懂地跟著抱了一大瓶滿天星的拿嬸離開了。
王家的後院顯然是有專人設計打理過的,奇石活溪,鬆竹蔭翳,盛夏之際依然日涼風清,別有一番幽靜。拿嬸帶著歡穿過蜿蜒小徑,也不知是不是小伊的循規蹈矩讓很滿意,心大好,熱地給因為一無所獲而失落的歡介紹起了院中木石,還手摘了枝酸杷遞來。
Advertisement
“老師,你放心吃,我們院子裏種的果樹都是沒打過農藥……”
拿嬸像是被誰掐住了嚨,聲音消失了一瞬,歡下意識順著的視線看過去,隻見蘿薜垂簾的深匆匆走過了一個戴著黑口罩的男人,手中拿了一個方形紙袋,正微佝僂著腰往花房方向去。
雖然拿嬸立刻又笑著轉過給歡說起了話,敦實的軀卻有意無意擋住了男人走去的方向,不過視力極好的歡在看過去的那一剎,恰好對上了男人沉的雙眼,還看到他口罩上沿一顆搶眼的黑痣。
也因為那顆在網上常被吹捧的所謂淚痣,歡頃刻間把口罩男的眼睛和案卷裏孟東勒的照片對上了,忍不住長腦袋追看過去想確認,拿嬸把滿天星高高地塞到了的手裏,一大蓬星星點點的小白花完全遮住了的眼睛。
“老師,你看什麽呢?”
歡回神,對上了拿嬸皮笑不笑的臉,搖擺的樹枝在臉上投下了變幻的暗影,顯得打量的目越發瘮人,歡生出了猶如小知危險的本能,幹脆大方地指了過去。
“剛才那人戴著口罩怪怪的,小伊一個人在花房呢,要不要去看一眼?”
拿嬸探究的意味不減,隨口答道:“那是家裏的花匠,因為臉上嚴重過敏怕嚇到人才戴的口罩。”
“哦,那我們走吧,我哥的司機還在外麵等著呢。”
率先往外走去,卻覺拿嬸森冷的目如附骨之疽盯在後背,盯得汗一豎了起來。
“老師,還有酒沒拿,米酒是王總找老師傅按古方釀的,外麵輕易喝不著。”
拿嬸手按在肩膀上,力道很,卻毫掙不了,歡的鼻尖冒出了汗珠,想起蘇睿的叮囑,腳下一崴直接跌坐在地,手中的花瓶也應聲而碎,抱著腳踝哼唧起來。
Advertisement
“老師,你沒事吧?”
拿嬸的手才到腳踝,就尖兩嗓子,大聲起來。
“哎喲,別,別,痛!痛!你等我緩緩。”
鬧出這麽大靜,自然有王家做事的人趕過來,有人麻利地撿起了地上的玻璃碎片,有人幫忙抱起了花,而在歡誇張的裏,形龐大的拿嬸居然輕鬆地把抱了起來。
“你要幹嗎!”
歡聲音瞬間拔高八度,覺自己陷進了一片裏,還是冰涼得像冷一樣的,嚇得頭發都要豎起來了。
“老師,你痛得背都了,我帶你去上藥。”
“不用,不用,我歇一下就好……啊!媽呀!”
歡急得要哭了,忽然被另一個溫暖、帶著汗味的懷抱給接手了,一抬頭看到陸翊坤著氣卻焦急關切的臉,還有他跑出來的滿頭大汗,心瞬間踏實了。
陸翊坤剛到門口,就聽見歡的大,都來不及向保安表明份,拔闖了進來,現在看基本完好,就是上被玻璃碎片劃了幾道痕,長舒一口氣。
“丫頭,沒事別,老人家心髒不好,經不起嚇!”
隔著薄薄的T恤,正在陸翊坤左的歡果然聽見了他激烈跳的心髒,怦怦地像鼓槌敲擊著的耳,卻特別有安全。用口型說了“對不起”三個字,可憐兮兮地,像招財貓般把手放耳邊啄了兩下米,陸翊坤嚴肅的麵孔就裂出點笑意來。
頭一回有人輕描淡寫地就從手裏奪過“東西”,拿嬸也愣了兩秒,才抬手要有作,陸翊坤雙手穩穩托住歡,腳下往拿嬸膝蓋一踢再一帶,近二百斤的婦人就斜摔出去了。
這時,追著陸翊坤的保安才趕了過來,因為不明況,看到倒在地上的拿嬸,立刻揮著腰間的子圍攏上來,陸翊坤兩腳先踹飛了兩個,歡看他們倒地以後痛得蜷一團的姿勢,都同地倒吸了口氣,餘下幾個看這架勢一時也不敢上前了。
Advertisement
“連我是什麽人都沒弄清楚,你們就敢手?”
陸翊坤目淩厲得像變了一個人,有冰封千裏的寒意,可被他牢牢護在懷裏的歡卻恨不得鼓掌大喊“好帥”。他兒不理會拿著對講機招呼同伴的保安,讓歡掏出他兜裏的手機,語音撥通了王德正的電話,一句廢話沒有,直接氣發問。
“王總,我妹子在你家摔了,我要帶走,行不行?”
說完,他拋了個眼神給歡,歡會意,按下了免提,陸翊坤確定已經焦頭爛額的王德正不會想在這個節骨眼上再和他正麵杠上。
果不其然,電話那邊短暫的安靜後,王德正彬彬有禮的聲音傳來:“怎麽會發生這種事?伊紋和拿嬸呢?我一再代要好好接待你們,老師怎麽還摔跤了?摔得嚴不嚴重?我找人送你們去醫院。”
陸翊坤的語氣罕見地冷:“不用,我家司機就在外麵,隻是我和你家的人發生了一點小誤會,你不會介意吧?”
“當然不會,有誤會也一定是我手下沒搞清楚況,您先帶老師走,我改天再登門致歉。”
掛掉電話,陸翊坤抱著人就往外走,狐假虎威的歡居然還手指了指被抱在他人懷裏的滿天星:“陸哥,小伊送我的花。”
陸翊坤眼一橫,說了句“喊給你送車上來”,抱著人就往外走。
拿花的人被他氣勢所懾,戰戰兢兢看了眼痛得依然起不了的拿嬸,見點了點頭,立刻小跑著跟了上去。
已經發了車子在等的蘇睿一看歡是被抱著出來的,先是一驚,繼而看到居然手在給陸翊坤比畫什麽,而陸翊坤也是副天塌下來老子都頂得住的表,就放下心來。等兩人上了車,接過花,居然還有個保安又提了兩壇子小米酒跑來,還滿臉賠笑,蘇睿是在牛皮哄哄地坐在後座的陸大爺上看出了打劫的土匪氣。
車子一開,陸翊坤從蘇睿包裏翻出儀,把車上和三人上都掃了一遍,確定在王家停留期間沒有加點東西帶走,歡開始講和小伊見麵的況,因為停留時間短沒太多可說的,車子還沒駛出盈江大道,歡就已經把前前後後都講清楚了。
“花、膠帶和花瓶呀都是拿嬸找人去隨便選的,不過膠帶是小伊自己的,拿嬸幫我抱花的路上還把枝葉都掰開看了。”
蘇睿掃了一眼放在前座的滿天星,枝幹上的膠帶被了一個工整的“×”形:“木上加‘×’,這個不難猜,還有兩壇小米酒……”
他臉一沉,問道:“陸翊坤,小米是不是又粟?”
“對。”
“小米酒是粟酒……還有什麽……”蘇睿的手指輕輕敲著方向盤,“能接的東西很有限,也設不了太麻煩的暗號……花本來是放在花瓶裏的?”
“對,一個明的四方花瓶,大概這麽高這麽寬,還說得不好看,讓我回家調整一下。”
歡比畫兩下,還想再仔細形容,蘇睿已經急打一個方向,往州民開去,同時撥通了龔長海的電話:“龔隊,請設法讓陶金知道王德正已經起了殺心,我們必須馬上行,而且孟東勒就在王家,可能是和王德正一道從瑯國回來。然後派兩個便帶證件到州民等我們,我們需要去學校搜查取證。”
本來還在撥弄那兩壇酒,想看看罐子上有沒有玄機的歡驚得酒壇都跌落了,幸好陸翊坤手快接住了才沒被砸到腳。
“小伊‘說’什麽了?”
歡艱難地開口。
“王德正起殺心了,要瞞住素瓦手,按他的慣例,應該最後會把責任推給素瓦。”
聽懂了的陸翊坤取出紙筆,在白紙上寫下“滿天星”“粟酒”,然後在天字下加了個花瓶式樣的“口”,旁邊寫下一個“木”,然後比著膠帶在上麵畫了“×”,然後再調整了一下幾個字的順序。
紙上變了滿(瞞)吞,殺星(心),粟(速)酒(救)。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90 章

重生后,渣總追妻火葬場
雲桑愛夜靖寒,愛的滿城皆知。卻被夜靖寒親手逼的孩子冇了,家破人亡,最終聲名狼藉,慘死在他眼前。直到真相一點點揭開,夜靖寒回過頭才發現,那個總是跟在他身後,笑意嫣然的女子,再也找不回來了。……重生回到18歲,雲桑推開了身旁的夜靖寒。老天爺既給了她重來一次的機會,她絕不能重蹈覆轍。這一世,她不要他了。她手撕賤人,腳踩白蓮花,迎來事業巔峰、各路桃花朵朵開,人生好不愜意。可……渣男怎麼違反了上一世的套路,硬是黏了上來呢……有人說,夜二爺追妻,一定會成功。可雲桑卻淡淡的應:除非……他死。
215.7萬字8 322367 -
完結1890 章

許你情深深似海
為了得到她,他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將她拉入他的世界。 他是深城人盡皆知的三惡之首,權勢滔天,惡跡斑斑,初次見面,他問她:「多少錢?」 ,她隨口回答:「你可以追我,但不可以買我」 本以為他是一時興起,誰想到日後走火入魔,寵妻無度。 「西寶……姐姐,大侄女,老婆……」 「閉嘴」 心狠最毒腹黑女VS橫行霸道忠犬男
342.7萬字8 29518 -
完結77 章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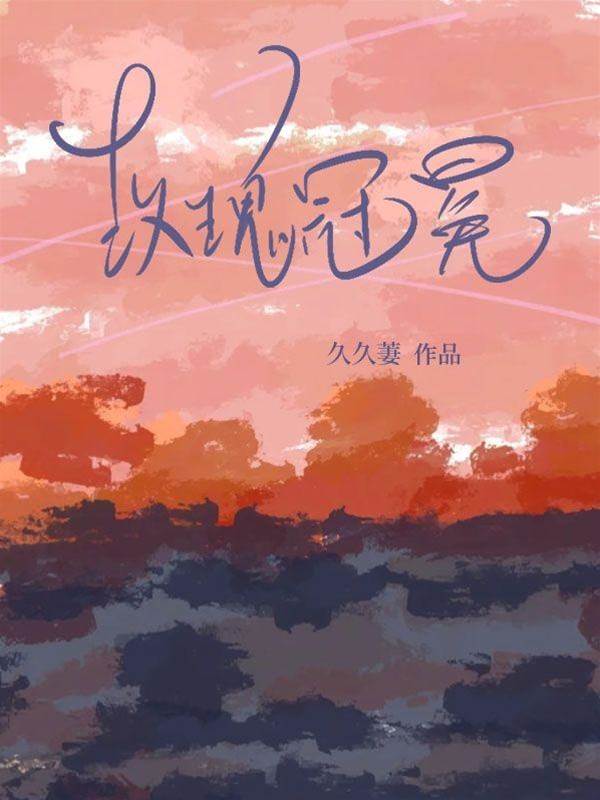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66 章

思餘如潮
孤冷學霸孤女VS冷漠矜持霸總父母雙亡的孤女(餘若寧),十一歲被姑姑接到了北城生活。後來因為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餘若寧嫁了沈聿衍。有人豔羨,有人妒忌,有人謾罵;當然也有人說她好手段。殊不知,這是她噩夢的開端。
15萬字8.18 2415 -
完結159 章

情疤
【落魄千金VS黑化狗男人】溫家落敗后,溫茉成為了上流圈子茶余飯后的談資。 橫行霸道慣了的千金小姐,一朝落魄成喪家敗犬。 是她應得的。 傳聞圈中新貴周津川手段狠辣,為人低調,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 無人知曉,當年他拿著溫家的資助上學,又淪為溫家千金的裙下臣。 動心被棄,甚至跪下挽留,卻只得來一句“玩玩而已,別像只丟人現眼的狗。” …… 溫茉之于周津川,是他放不下的緋色舊夢,是他心頭情疤灼灼。 既然割不舍,忘不掉,那就以愛為囚,相互撕扯。
28.6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