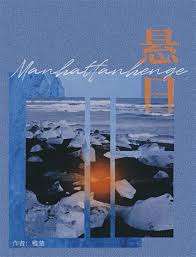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斬尾》 104
姜荔的眼睛猛然一亮,又暗淡下來,說:“怎麼會有如此神奇的靈藥。”他把沉重的蛟弓放下,走到一邊坐下休息,上上已經出了一層薄薄的汗,也開始酸痛。姜荔心中空的,他說:“就算有,也是神仙。”
“你說的倒也沒錯……”姒洹說:“北海之北,南極之南,有不死仙草,系神軀所化,可修復世間一切傷痛,名為長生。”
“這聽起來像一個傳說。”
“的確是……傳說始祖之地,就生長著這種長生草。”
姜荔心里猛地一跳。
始祖之地,沒有媧族裔不知道這個地方。傳說這是神初降之地,神從天上降至人間,便落到一片荒蕪之中。而后繁衍出代代的神裔,逐漸從始祖之地走出。所以始祖之地可謂是八族共同的源頭,但可惜族群早已忘記了這個地方,只變了一個傳說,沒有人知道怎麼去。到傳說中的地方找一種傳說中的仙草,無異于癡人說夢。
姜荔幾乎要樂了,這像是哄孩子的話,他說:“你知道始祖之地在哪?”
“這上面記載了——”姒洹揚了揚手里一張年代久遠的樹皮,說:“上面說,只要朝著北辰星的方向一直走,走到大陸和海的盡頭,星辰之下,便是始祖的地方。而始祖之地中生長著長生草,可以消弭神人一切傷痛。”
這聽起來更不靠譜了……姜荔說:“有人去過嗎?這個路線是正確的嗎?”
姒洹搖搖頭:“手札上記載了……只要朝著北方一直走,自會有母神的魂靈指引著子孫前進。”
“……”
姒洹握住了姜荔的手:“這是母親留下的典籍,我想,留給我們,是有一定的緣故的。”
“你難道不想,恢復你所有力量,自由自在,肆意戰斗,再也不為斬尾之痛困擾?”
Advertisement
……
這聽起來是一個相當瘋狂、而又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其中蘊含的力非常巨大,幾乎是正正切中了姜荔心中最深切的,他心中最想要什麼,最關切什麼,最得到什麼。自斬尾以來,姜荔早已將戰士的過去深埋在心底,幾乎不曾想過有再回到過往的可能,但這并不代表他不想要回自己的力量,要回戰士的自由和榮耀。只是這種驚喜太過突然和虛浮,讓姜荔也不得不開始懷疑起來。
“這到底是真是假,姒洹?”姜荔不太相信,“你會讓我恢復力量嗎?”
“你不怕我恢復力量后……第一件事就是殺了你們!?”
不得不說,從姜荔來到姒族的第一晚,他就沒放棄過殺害他們的想法,也幾度重傷姒洹。只是由于力量所限,失敗罷了。但其實姒洹也很想提醒姜荔,他當初為之掙扎的目標已經不存在了,妹妹文姜已經順利繼承了家族,現在殺他們也是多此一舉,但姒洹只說:
“如果那樣,那就是我們的失敗了。”
姜荔說:“這只是個傳說中的傳說,從來沒有人去過,或真切地聽過始祖之地的消息,這個記載不一定是真的。況且,即便始祖之地中真的有長生草,能否治愈人的……也是未知之數。”
“但這的確是一希,不是麼?”姒洹說,“而且是你想要的希。”
姜荔回想起他長尾尚在之時,渾充滿力量,在草野中來去自如,輕如飛燕、狠狠斬殺仇敵的痛快。蛇人神巨大的蛇尾,宛如最鋒利的武,橫掃之所向披靡;一會又憂愁這只是一場空,水中撈月,懷揣了希而后又被狠狠摔碎,反而比之前更失落。說不定還會招致更糟糕的禍患……
Advertisement
不知何時,姒沅從他后走了出來,抱住了姜荔大半個子。他說:“只要是荔想做之事,我都會盡力為你完。”
“無論你去哪,我都會陪你走到盡頭。”姒沅說。
“我能離開嗎……我是說,你們會讓我離開姒族?去尋找一株縹緲無據的仙草……”
“相信我,小荔枝”姒瀧和大哥對視一眼,又握住了姜荔的肩,笑道:“沒有別的事比你更重要。”
“你現在有這個權力。只要你告訴我們想不想要,刀山火海,上天地,我們也會為你取來!”姒瀧說。
在幾人的勸說之下,姜荔也是真的了心。就如姒洹所說,即使只是如縷一般的希,但能夠愈合他的斬尾之痛,讓他回復以前的日子,無論如何他都會拼命抓住。他甚至來不及考慮背后有什麼理由或者不在乎有沒有陷阱,只要能讓他恢復,他都愿付出代價!極夜前后那段不斷衰弱的日子,又被困在樓中不斷生育以續命,姜荔以為他的心已致絕境。但現在,他才知道,他心里還是有奢的,只是這奢埋得太深而從來不敢想……
眼看著幾個舅舅紛紛表態,愿意陪姜荔一起去找長生草。姜荔也被說得了心思。姒旦在后面越看越著急,忍不住踹了一腳還在傻站著不知想什麼的姒,趁著沒人注意嘀咕了幾句:
“還愣著干什麼啊?去啊,說我們也去。”
再不在姜荔面前刷刷存在,他們的位置可要被舅舅得沒邊兒了,姒旦心里打著小算盤。都說新人比舊人好,舅舅可別以為他們地位就一定穩了。
姒才反應過來,說:“既然這樣,我和旦也去。路途兇險,多幾個人也好,多份保障。”
Advertisement
看到姜荔的目終于看向了這邊,旦輕咳幾聲清了清嗓子,淡笑道:“這麼有趣的事……舅舅們可不能把我和拋下。”
“我們也要去。”
第74章 7.3 始祖之地
旦把拉到了一邊。
眼看著舅舅們和姜荔都走了,旦對還有些悶悶不樂的說:“愣著干什麼呢,我們也準備去。“
看起來興趣卻不大:“何必呢。”他慢慢地也走開了,說:“我們都離開了,族中怎麼辦?況且,去找一個傳說之地,你也聽到了,沒有人去過那兒……”
旦是的弟弟,脈相連,對于兄長的小心思,可謂是若觀火。他說:“那怎麼著?等那姜族人回來,怕不是連我們什麼都忘了。至于族中之事,大舅舅都不擔心,你怕個什麼。”
姒說:“我不是怕!只是……他本來就不記得我。”
自從回到姒族后在冰河上重逢,姜荔就好像對他沒什麼印象。也許在他心里,還稱不上一個對手,沒有威脅,自然也不放在眼里。即便到了現在,姒在他心里的印象,恐怕還是一個小輩而已吧。一掌打到了巖壁上,緒波,巖壁也他被溢出的靈力化作了一攤冰水,淌了下來。
旦可比他還不如呢,留下盡是壞印象,但他不像兄長那麼憂心忡忡。現在姜族人的地位水漲船高,舅舅們被迷得五迷三道,他們的大靠山祖母又不在了,姒旦第一次有了那麼點危機。但開葷之后,年人的心思卻不再是孩時那種惡作劇式的惡意,反而更多地歪向了其他地方,變得浮想聯翩、勾連纏綿。而游歷給他最大的收獲便是,如何將這種惡意藏起來,在外表上表現得風度翩翩、溫文爾雅,心里的小心思可一點不。
姒旦說:“你不想要自己的蛋了?”
姒的耳朵紅了一下,了,低聲道:“我自然想要,只是……”
“想要的話,靠雄自己可不能把蛋生出來!”姒旦說。
“我當然知道!你可別來,旦……“姒說。
“誰說我要來的?”姒旦說。他倒是想,可舅舅們也不讓吧!想起二舅舅冰冷冷的目,大舅舅一言不合就下黑手……就算三舅舅很寵他們,現在有了自己的蛋,也不會像以前那樣了吧……說起來舅舅們也是很過分,剛開始時哪個沒干過壞事,現在卻都收起來壞模樣了,一個個溫款款賢良淑德的,出門能讓人驚掉下。他們倒是先行一步吃到荔枝了,現在卻轉頭把橋都拆掉不讓別人過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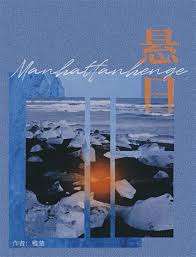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