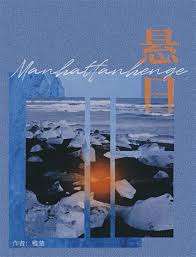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假駙馬,真皇后》 206
“……可是這樣的惡氣,那時太祖皇帝已然稱帝,富有天下,他得是因他不介意,孤若還心,卻要什麼都沒有了,孤又為何要?”
“孤可不會聽信什麼兄弟深、七王輔政的故事,后頭高祖皇帝為了把這些個藩王都收拾掉,費了多大功夫?父皇當年若不把幾位叔伯清理了,如今又豈能做得這位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父皇自己都不曾相信、更不曾力行的所謂道理,倒要拿來教訓孤,說到底,不過是父皇的心已偏了罷了!”
太子話音一畢,同坐車廂里的岳懷珉已然是變了神,悚然道:“殿下,慎言!”
雖說此刻車上只有他們二人,但前頭還有馬夫,殿下這樣駭人聽聞的言語,一旦傳出去可還了得?
然而裴昭元卻只是閉目淡淡一笑,道:“事到如今,孤又還有什麼好怕的?”
“孤與父皇……早已是彼此都心知肚明了。”
---------
恪王府。
時近正午,日頭高懸,還好十一月的天氣并不熾烈,即使是這麼直愣愣的曬著,也尚且不算熬人。
管事清點了行頭,又親自指揮著小廝、婢仆們裝箱收拾東西,這座王府本就不是很大,此刻人來人往更是顯得忙碌熱鬧。
王府只有一個主子,恪王殿下就是王府的天,眼下王爺接了旨又要往北地辦差去了,這一去也不知得忙多久,北地不似南邊富庶、產魚米饒,帶的東西自然是越多、越全越好。
其實這位管事來王府也不很久,雖說他名頭上是管事,但無奈恪王殿下實在過于勤勉,朝務忙起來,能整日都在衙門里打轉,過夜也是不回來的,好不容易辦完差事,偶爾能休沐了,還要往公主府里去,是以管事也沒見過幾面王爺,得一回機會在他面前辦差臉,更是難上加難。
Advertisement
眼下自然格外上心。
裴昭珩醒來,等小廝伺候他更了、洗漱完畢,走出門看到的就是王府中這樣忙碌的景象。
管事見王爺出來了,連忙湊上前來,從袖口里出一個單子遞了過來,低眉順眼臉上堆笑道:“王爺看看,這些東西可還夠用,要不要再添置點什麼?”
裴昭珩接過那張單子,只草草掃了兩眼,便遞了回去,淡淡“嗯”了一聲,道:“夠了,不必再添。”
管事見他滿意,心中一喜,接過那單子揣回去正要轉,卻又被恪王殿下住了。
“等等。”
管事有些茫然,道:“王爺……可是還有什麼吩咐?”
裴昭珩道:“……廚子,帶上。”
管事頓時有些丈二和尚不著頭腦,恍然片刻卻忽然想起,先頭陛下剛下旨王爺去北地時,王爺似乎的確他們去尋過廚子,要求還很古怪,要會做糖醋小排、叉燒、醬肘子,還至得是京畿一片數一數二的滋味——
可王爺平日,瞧著也不怎麼吃甜啊?
管事道:“可是之前王爺吩咐找來的那做甜口的廚子?”
裴昭珩“嗯”了一聲。
……
自子環去了昆穹山營地,只來過一封書信,寫的還頗為潦草,其間把那請他吃飯的周將軍很是編排了一頓,又奚落了一道接風宴難吃的,一桌子的菜竟沒有半道能讓他有夾第二筷子的,最后飯也只拉了兩口。
子環臨走前,裴昭珩便覺得他胃口不知為何不太好,至和以前相比,大大不如,也不知道是怎麼了,本來就不好好吃飯,眼下到了北地飯菜不合口味,怕是更有借口挑食了……
人是十八了,心智卻還是個孩子。
子環似乎總是如此。
Advertisement
……即便是在近日裴昭珩做的那些奇奇怪怪卻又似乎并非完全無跡可尋的夢中,也是如此。
裴昭珩想及此,微微有些恍神。
也許是這些日子的確太累了,也許是疲憊以及、又是在掛念,每每閉目養神時,他腦海里總能看見一些古怪的畫面,而且還都無一例外,全部和子環有關。
只是產生一時的遐思、幻覺也就罷了,可夜間夢,也開始變得全是賀子環。
只是夢境卻要比那些閉目時忽然浮現眼前的畫面要長久、且真切的多,甚至有時候都真切的能人忘記他置于夢境之中。
夢中的子環千姿百態,除卻他們初相識時,長街上那驚鴻一瞥,那個眉目廓分明、五帶著年獨有的、襯托出幾分憨直的圓鈍的賀子環……
竟然還有許多別的模樣。
而且那些夢中的景,裴昭珩分明從未見過,卻又詭異的覺得悉。
其中一個地方,是崇文殿座后的屏風——
裴昭珩會認得那里,還得歸功于他做“長公主”時和賀顧的婚事,那時他便是從英鸞殿的屏風后走出去,與賀顧拜過天地、拜過帝后、結為夫妻的。
夢中的屏風與英鸞殿有所不同,后殿更大幾分,這樣規制的宮殿,只有百朝會的崇文殿才有,這些日子裴昭珩沒落下過一場朝會,自然認得擺設風格。
然而這樣一個肅穆開不得玩笑的所在,夢中他與子環竟然在這地方,隔著一道屏風,在文武百的面前——
自記事以來,裴昭珩一直寡思,如今,還是頭一回做這樣的夢。
……還好這樣的事也不算夢的全部,這夢也有其他的容,只是那些容,就不怎麼讓人覺得愉快了。
Advertisement
夢中不愉快也就算了,讓人不愉快的人,竟然離開了夢境,又很快找上了恪王府。
太子帶著岳家的大公子來了,還拉著兩三車的東西,說什麼也要恪王臨走時帶上。
裴昭珩雖然早知道這位大哥遠非平日里表現出的,也知道他害過陳皇后、甚至當年皇姐之死,多半也和姨母不了干系,然而兄弟相見時卻從不表出怨懟,且也分毫不提這些事,只做全然不覺的模樣——
但此刻他看見大哥那素日里瞧慣了的,總是溫文爾雅帶著笑意的臉——
視線里這張臉卻不知為何,忽然詭異的變了神、變了形狀,變得不再那麼笑意盈盈、噓寒問暖,只剩下十十的狀若癲狂、惱怒、和分毫不加掩飾的恨意。
他死死盯著自己,嘶吼著、咆哮著,頭發散落著,蓬而狼狽,再不像是那個風度翩翩的貴公子,反倒像是一條落了難的豺狗。
……
“你謀朝篡位,弒君弒兄,大逆不道,便是坐上了皇位,也是名不正言不順,你以為你就能在這個位置上,坐的穩了?朕告訴你,你是在做夢,朕是不會給你寫傳位詔書的,朕絕不會寫……朕決不……”
“大哥不想寫,便不寫吧。”
“你……你就不怕日后,有人說你……說你的皇位得來不正,你就不怕旁人謀反討伐?你就不怕……”
“大哥殺忠良、信佞,母后何曾害你?聞貴妃何曾害你?錢大人、陸大人何曾害你?便是二哥與你相爭,也從來都是明磊落、堂堂正正、從不曾使過私歹毒手段,大哥卻能將他們都殺了,又害了二哥妻兒,連親侄子也不放過,大哥喪盡良心,天理不容,你都不怕,我又有何好怕?”
……
這段爭辯,此刻無比清晰的出現在了裴昭珩的腦海里,然而卻也只有這樣一段,他再想往下繼續想,卻只覺得頭痛裂。
而眼前太子那張扭曲的臉,也一點點恢復了真實模樣——
春風化雨、角微彎,風度翩翩,親和寬厚。
“……三弟,此去又要辛苦你一趟,以前你最怕冷,如今雖然好了,但北地苦寒,也該好好留心,千萬別熬壞了子。”
“大哥給你備了點東西,雖然不算多厚周到,但吃的用的,多也夠一路花用了,你可莫要再推辭。”
太子笑著,語重心長道。
---------
轉眼間,已是進了十二月。
天氣愈發寒冷,賀顧的瞌睡也越來越多,好在昆穹山營地差事閑,運糧也不必一個月不歇的忙活,通常忙完了那四五日,就能有個起碼十來日的清閑。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700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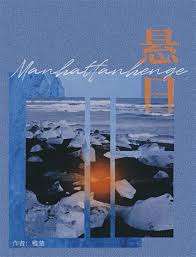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