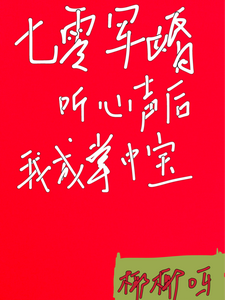《一胎又一胎,說好的禁欲指揮官呢?》 第23章 只要他愿意
只是,還沒有正式回到復讀班,想做英語家教,恐怕還需要回到學校重新考試,拿出點兒底氣來才行。
許長夏正琢磨著,孫紅英繼續熱道:“我剛才聽你說,你舅舅是開養場的?”
“對。“許長夏點頭回道。
“那你以后能不能每隔一禮拜,給我捎一兩斤蛋來?我弟弟正在長,按糧票拿蛋真是不夠他吃的!”
送上門的第一筆大生意,許長夏哪兒有推掉的道理?
想了下,道:“我直接給你送到家門口吧?省得你跑來跑去的,蛋又容易破。”
“那當然好呀!”孫紅英開心地點頭應道。
許長夏不怕麻煩,也就是多走幾步路的事兒。
而且,這不就是二三十年后面華夏國興起的送貨上門?某團?
朝孫紅英笑笑道:“那就這麼說定了,我給你七一斤!你家在哪兒呀?”
“七一斤你不就吃虧了?對面供銷社一塊一錢一斤呢!而且你還得單獨跑我家去,我給你七五一斤!就這麼說定了!”孫紅英沒給許長夏反駁的機會。
“我家住在公安大院,五棟是我家!待會兒我家阿姨來了你跟混個臉,除了買菜時間都在家里,你隨時送去都行!”
原來孫紅英就住在公安大院。
“那你們怎麼繞遠路來這兒買菜呢?”琢磨了下,有些不解地問道。
“我們那兒菜沒有你們這兒的好,你們這邊的菜出了名的新鮮品種多,而且不瞞你說,有些阿姨會拿著主人家給的菜錢買便宜的菜以次充好,中飽私囊,所以我們那邊菜市場的菜,品質會差一點兒!”
孫紅英倒是個直腸子的爽快人,有什麼就說什麼。
“原來如此……”許長夏若有所思點了點頭。
怪不得,在這兒賣了好一會兒的蛋,都沒看見幾張面孔。
Advertisement
做生意首先得看所在市場的人流量,觀察了好一會兒,六點左右的人流量確實很大。
后面幾天,就先留在這兒賣蛋試試。
兩人說話間,孫家保姆買好了菜走了過來,聽說許長夏能送新鮮蛋上門,愣了下,隨即朝不遠招呼了聲:“趙嬸子!你過來!”
一位中年婦隨即應聲走了過來。
“這個小姑娘是我家紅英小姐的同學!家開養場的,可以每星期送一次蛋到我們家門口!”孫家保姆朝趙嬸子熱地推薦道:“你家孩子多,不是說蛋不夠吃嗎?”
“對!”趙嬸子一雙四的眼睛朝許長夏打量了眼,問:“你家蛋什麼價格啊?”
“七五一斤。”許長夏笑了笑,回道。
“那確實劃算,比供銷社便宜了三五一斤呢。”趙嬸子點了點頭。
“那您要定嗎?”許長夏客氣地詢問道。
“定,你下次去紅英家的時候,給我也捎上三四斤,我家住在十六棟。”趙嬸子點點頭回道。
三四斤!!!
一禮拜三四斤,一個月不就要十五斤?
許長夏瞬間瞪大了眼睛。
“他們家人多得很,五個孩子,加上老太太和夫妻兩個,一共八口人,就靠那點兒糧票哪兒夠吃的呀!”孫家保姆笑著解釋道。
“那行,多謝您了阿姨,給我介紹這麼大一筆生意!”許長夏隨即甜道謝。
“蛋不行的話我下回可不買的啊。”趙嬸子在旁又道。
“肯定不會差的,放心吧嬸子!”許長夏拍著脯給打包票。
等到兩人走開了,孫紅英匆匆忙忙朝許長夏小聲叮囑了句:“趙嬸子那張可不是好惹的,你要小心一點兒……”
許長夏愣了下,點點頭回道:“好,我記住了,那我這周六給你們送蛋去。”
Advertisement
收下了孫家和趙嬸子各自給的一塊錢定金,加上之前賣空蛋老母的九塊一,一共掙了十一塊一錢,心滿意足地揣好了錢,拎著兩只空空的菜籃子回了許家。
許芳菲已經蒸好了包子,探頭看了眼許長夏手中的籃子,有些吃驚:“一個小時不到你就賣空了?”
一上來就來了個就開門紅,許長夏心里開心得很。
“今天運氣好!供銷社明天蛋漲價!”
說著,將賺來的十一塊一分出來一半給了一旁許勁:“三舅,剛剛咱們說好了的,利潤對半分。”
許長夏是要帶著許芳菲和許勁兩人一起過好日子的,絕不會讓許勁吃虧。
許勁卻又把錢推了回來,道:“等你們租好了房子之后,咱們再仔細算。”
許長夏一想,也是,現在正是缺錢的時候,等以后再多補一些給許勁。
把錢給了許芳菲,上只留了五塊錢,去海城肯定要用得上。
收拾好了吃完早飯,陸副已經提前在門口等著了。
“陸副你稍等我兩分鐘!”許長夏正在房間里換服,朝陸副招呼了聲。
“不著急!接送你們去海城,這是今天長待給我的唯一任務!”陸副樂呵呵地回道。
許長夏換好昨天江耀給自己買的服,許芳菲剛好替他們裝了十幾只包子送進來。
“昨天就忘了說,我兒穿這服可真好看!”許芳菲看著落地鏡里的許長夏笑瞇瞇道。
“等咱們賺了錢,我也去給他買一西裝。”許長夏朝許芳菲回道:“然后和他一塊兒去民政局拍結婚照。”
“你看你這孩子,說話一點兒也不害臊!”許芳菲低了聲音,嗔怪地瞪了許長夏一眼。
“我說真的,只要江耀愿意,我就跟他去領證!”許長夏認真回道。
Advertisement
昨天早上從江家回來,其實就是打算回來拿戶口本的,結果各種事打了的計劃。
但是這樣也好,后來仔細想了想,緩幾天也不打。
有了基礎的婚姻更牢固。
許長夏和許勁坐到車上時,許長夏立刻給陸副遞過去了兩只熱騰騰的包子:“一只梅干菜的,一只桂花豆沙的,你嘗嘗?”
“謝謝許小姐,我沒有忌口,都吃!”陸副立刻紅著臉接過了。
許長夏是想讓旁人也嘗一嘗許芳菲做的包子,看是否符合大眾口味。
看著陸副吃完了,試探地問道:“怎麼樣?好吃嗎?”
“好吃!”陸副點點頭回道:“要是桂花味兒更重一點兒的話,也許會更解膩!”
“行。”許長夏記住了。
“我……我不是……”陸副是順口就說出來了,以為自己說錯了話。
“別怕,我沒有其他意思的。”許長夏將手里的一只大飯盒順手遞了過去,道:“這兒還有八只,你帶給你們同事也嘗嘗?他們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你就告訴我!”
陸副朝許長夏看了眼,有些疑。
許長夏這意思是……
他似乎約有點兒明白,但又不確定,他立刻將飯盒收好了,放在了顯眼的位置,以免自己忘記。
一行三人隨即出發了。
車開了好一會兒,許長夏看著路邊經過的一個派出所,忽然想起早上許芳菲說起的那件事。
隨即扭頭問旁的許勁:“三舅,你知不知道是誰把許路原打暈過去的?”
“咳……”正在開車的陸副忽然嗆咳了聲。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3 章

趕在春風之前擁抱你
我守萬家燈火,也想守心愛的姑娘。1.聞希第一次去海城公安大學,就撞見剛從訓練場出來的江礪。彼時江礪穿著一件被汗水浸濕的黑色背心,肌肉結實的小臂裸露在空氣中,目不斜視,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濃烈的荷爾蒙氣息。同行的室友屈起手肘撞了下他,“礪哥,那邊有個妹子在看你。”江礪抬眸,淡淡地望了聞希一眼,“有空看妹子,不如想想你的十公里負重跑怎麼才能及格。”不久后,有人看到在隔壁A大,江礪背著服裝設計系的系花聞希繞操場負重跑。他聲音低沉,偏頭去看伏在他背上的姑娘,心里躁得慌, “你什麼時候答應做我女朋友,我就什麼時候放你下來。” 2.公安大學人人都知,刑事偵查四年級的江礪不光拳頭硬,脾氣更是硬得不行。但只有江礪自己知道,每每聞希窩在他懷里朝他索吻的時候,一身硬骨全部化作繞指柔。 【軟甜小仙女婚紗設計師vs嚴苛硬漢刑警隊長】大學校園到都市/礪哥撩不到你算我輸/甜到掉牙
28.8萬字8 26039 -
完結106 章

紅塵滾滾滾(軍旅)
宋星辰看见苏清澈的第一眼,就恍惚有种感觉:这个男人太危险而宋星辰的第六感一向比她的大姨妈还要准。所以当宋星辰这个长袖善舞的淘宝店长对上腹黑记仇的军官大人,除了咬牙切齿,就是恨之入骨惹我?没关系……于是,宋星辰很是顺手的把自己打包寄了过去。
28.5萬字8 6272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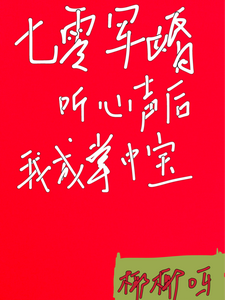
七零軍婚:聽心聲后,我成掌中寶
【心聲+年代+爽文+寵文+穿書+先婚后愛+七零+發家致富】 俞向晚穿成七零年代文中的炮灰。 新婚當晚,渣男被海王女主叫走,原主獨守空房,一個想不開,氣死了。 俞向晚:這能忍? 她當場手撕渣男,大鬧全家,奪回嫁妝,索取精神損失費,在新婚第二天離婚
19.2萬字8 5734 -
完結111 章

軍婚:跟首長閃婚後全豪門來團寵
【現言軍婚】【超級爽文】傳聞高嶺之花的軍區首長傅宴庭在戰區撿回來了一隻小野貓。野性難馴,盛世美顏,身懷絕技,吃貨一枚。傅宴庭就好這一口,直接閃婚,綁定夫妻關係,禁錮在身邊圈養,應付七大姑八大婆。京都吃瓜群眾評價:“毛病太多,沒有背景,早晚被傅家針對,掃地出門,淒慘收場。”哪裏想到這隻小野貓不簡單,不服就幹,絕不憋屈。剛領證就把首長壓在身下,占據主動權。進門第一天當著公公婆婆的麵掀桌。進門第二天就把挑事的綠茶打的滿地找牙。進門第三天就跟桀驁不馴的小姑子處成了閨蜜。進門第四天將名媛舅媽潑了一身糞水……被打臉的京都吃瓜群眾評價:“得罪公婆小姑子傅家親戚,看你怎麽死!”結果被寵上了天。公公傅盛銘:“家人們,誰懂啊?第一次看到我那個不可一世的兒子蹲下身給婆娘洗jiojio,笑瘋了。”婆婆林清月:“笑瘋了姐妹們,我兒媳婦的大師叔竟然是當年求而不得的白月光,現在還得低頭叫我一聲林姐姐呢。”被揍得鼻青臉腫的渣渣們集體到傅宴霆麵前哭訴:“首長,您女人都要把天給掀翻了!求您發發神威管管吧!”傅宴庭:“哦,我寵的。”
21萬字8 8962 -
完結163 章

驚!乖乖女錯撩渣男友小叔
【男主強制愛上位+極限拉扯+渣男追妻火葬場+軍婚雙潔】科研大女主+狂野深情大佬 徐初棠和宋燕京青梅竹馬,為他放棄大好前程,甘當他背后的女人,卻慘遭背叛。 她果決斬斷情絲,“我們取消婚禮,好娶好散。” 宋燕京想坐享齊人之福,偽裝專情,“我對你的愛,獨一無二。” 她沒戳穿,十五天后,她設計假新娘拿著他濫情的證據,替她完成這場‘騙婚’大局。 宋燕京慌了,發瘋了,翻遍全城,也沒翻出她的一片衣角。 再見面,她是高不可攀的科研大佬,國手鬼醫的繼承人…… 他紅眼跪求原諒,卻發現她身邊站著全國最尊貴的男人,他的小叔—宋乾州。 …… 宋乾州,軍界翻云覆雨,殺伐果斷的一掌堂,徐初棠無意牽扯。 可她在狠狽時會遇見他,躲過狂風大雨。 在她被攻擊時,他托舉住她,免去一場傷痛。 后來,因身份的禁忌,她要跟他劃清界線。 他趁機將人壓在車窗,抹著沾了他唾液的紅唇,說:“想渣我?得問全國民眾。” …… 都說徐初棠的紅顏禍水,勾得最有權力的男人罔顧人倫。 可只有宋乾州知道,他才是披荊斬棘勾到她的那一個。 (PS:純架空啊,純架空)
28.9萬字8 1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