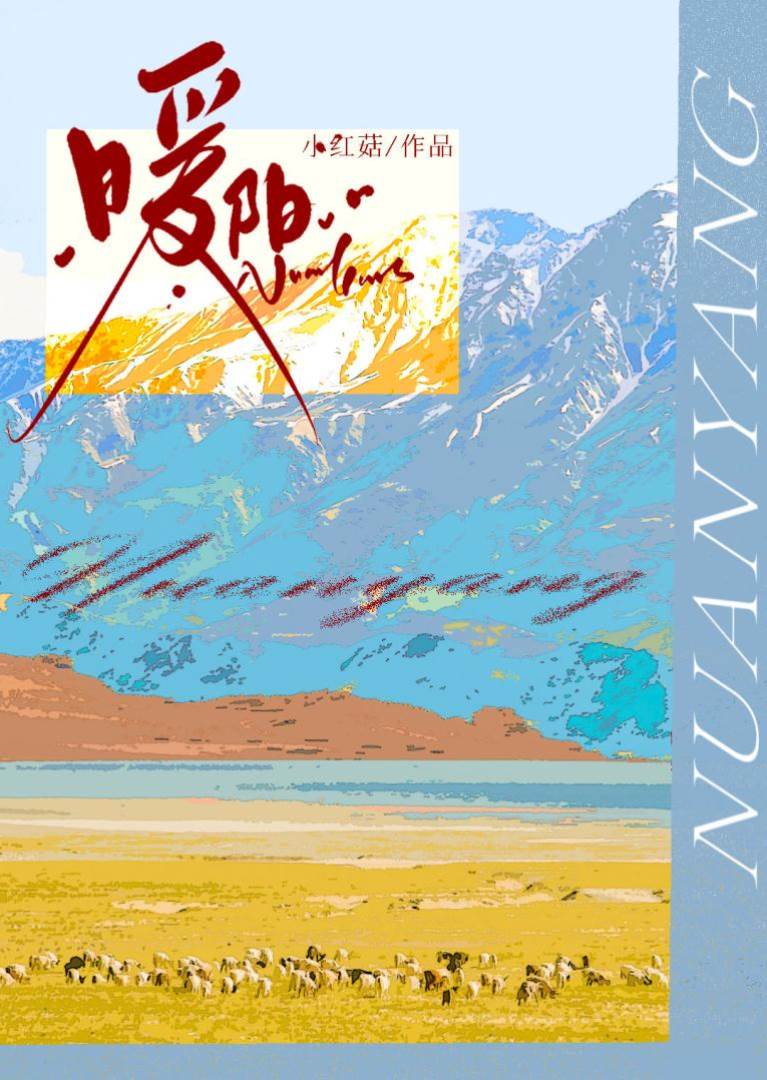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夢裏撩錯了前任的眼盲弟弟[救贖]》 “時安戴眼睛好好看色色色”
“時安戴眼睛好好看”
好不容易想到“英雄救”的辦法失效了,任誰都會不高興,但只是皺了皺鼻子,沒再說什麽,目掃向大黑狗,直接一掌拍到大黑狗腦袋上,打斷了它的咆哮。
“好可惡的狗,快走!”
大黑狗灰溜溜變了椅子。
“陶斯曜”沒說什麽,轉坐到了椅子上,用手指著那些鄭相宜看不懂的按鈕,他閉著眼睛就像個小瞎子。
鄭相宜好奇地問:“你唱歌前的流程可真多。這是你緩解焦慮的習慣的嗎?”
他盯著自己的手指也不說話。
鄭相宜被無視得徹徹底底了,這更加證實了的猜測。他或許看穿了在騙他。
早知道就直接用仙這個份命令他唱歌好了,何必瞎編什麽故事。他不會信的。
鄭相宜背對著他,臉上什麽表都沒有。
“陶斯曜”忽地轉,又彎了彎角。
鄭相宜試探著問:“你是不是猜到——”
他眨了眨眼,眸專注,聲音輕,“我猜到什麽了?對了,你剛剛不是問我為什麽唱歌前要做這些嗎?是因為我習慣了這麽做。”
鄭相宜張開又合上,過了會兒才說:“沒什麽。”
鄭相宜不想再提這件事了。
“陶斯曜”的神看起來認真的,不像是在和開玩笑。
他或許并沒猜到在騙他。應該只是想多了。
他突然問:“你怎麽知道我的事?”
鄭相宜臉平靜,語氣裏滿是理所當然:“仙無所不能。”
“哦,仙。”他學的語氣說話。
他眉頭挑了下,揚起了角。鄭相宜盯著他的臉,驀地心中一。
...
“陶斯曜”還是答應唱歌了。
夢裏是個大白天,在沒開燈的房間裏,他手指練撥著吉他弦,看著,全程沒有挪開視線。
Advertisement
這首并未發布的新歌只有一位聽衆。
鄭相宜不懂陶斯曜打的網球,也不敢他騎的機車。
如果不是因為考上同一所大學,或許連在背後默默注視他背影的機會都沒有。
的生活三點一線,和他富多彩的人生完全不一樣。
可現在能及到他了。
他唱完後仍看著,眼神失焦,似乎隔著在看其他東西。鄭相宜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又輕輕了他幾聲。
他分明的濃睫忽地眨了眨,“怎麽了?”
鄭相宜搖搖頭。
剛剛的“陶斯曜”給一種說不上來的覺,就好像陷了與世隔絕的狀態中了,下意識想要醒他。
還聽說陶斯曜吃甜食。
也喜歡。
這或許是和他唯一的共同好。在手中變出了兩支冰淇淋,自己率先嘗起了香草味的。
“吃冰淇淋嗎?”
之前媽媽管得嚴,鄭相宜其實也沒怎麽吃過冰淇淋。但是今天夢前特意買了一支兩塊錢的冰淇淋,覺也沒有媽媽說的不健康。也沒有胃疼。
“陶斯曜”淺淺地皺了下眉,他不喜歡吃冰淇淋,本想拒絕的,可及到臉上的笑容,不知怎麽就答應了。
他像只順的大犬般站起了,朝靠近,頓時將鄭相宜前的空氣扁。
陶斯曜手指一勾接過了手裏的冰淇淋,只吃了幾口。
他著快化掉的冰淇淋就著,好像怕被主人懲罰的狗狗。難道是不吃這個種廉價冰淇淋?倒是知道DQ什麽的,但沒吃過。
鄭相宜攥手指:“你不吃了嗎?”
他皺了下眉:“有點兒,冰牙齒。”
夢裏的一切覺都很真實,這就是夢的神奇所在。鄭相宜視線下移:“那你還用手,手不冰嗎?”
Advertisement
“陶斯曜”語氣裏帶了點說不上來的意味:“可它是你給我的呀。”
鄭相宜走上前拿走了他手裏的冰淇淋,輕輕揚起了角,認真地說:“不想吃就直接說嘛,你不說別人怎麽知道你在為難呢?”
這一抹笑容在“陶斯曜”眼裏卻顯得格外刺眼,冥冥中,他覺得不是在對他說話。
“好。”他又問:“那你有過這種為難嗎?”
鄭相宜沒回答,只是一個勁兒的催他唱歌。
說:“夢境馬上就要結束了。”
他頓了下,走到了話筒前。
一曲終了。
他的歌聲令鄭相宜突然想到了那個被錯過的舞。
“我們來跳舞吧。”
燈下,陶斯曜朝著走來的那一瞬間,實在令人難以忘記。
周圍的環境在鄭相宜的控制下隨之一變,從寬敞整潔的錄音室變了小包廂。
鄭相宜知道像陶斯曜這樣的男生是絕不會去街邊六十塊錢唱三個小時的小KTV的。在那天之前,只去過們小縣城裏的KTV,是在過年的時候和家人一起去的。所以篤定陶斯曜會不習慣。
但沒想到他會這麽不習慣。
狹窄的小包廂裏,只能容納三個人活,玻璃桌和鄭相宜將“陶斯曜”到了點歌臺上。
鄭相宜膝蓋頂他兩之間的牆壁上,睜著黑漆漆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他,聲音不同往常帶著點蠱的意味:“就在這裏怎麽樣?”
他呼吸一滯,莫名覺得有些熱。
眼前的孩好、純真,像一朵可、熱奔放的花朵。
他發幹,剛剛融化在舌尖的冰淇淋突然在裏冒起了甜香。
直到包廂響起歌曲的前奏,陶時安拍了拍手裏的話筒,餘瞥到屏幕提詞和點歌的屏幕,他才敢確定這是哪裏。
Advertisement
“這裏是KTV嗎?”
“嗯。”
鄭相宜突然湊了過來,陶時安嚇得往後一退,腰部直接撞到了後的點歌,發出咚咚一聲。
“你躲什麽?”鄭相宜手指在他後按了按,“我只是調下音量。調好了,來跳舞吧。”
沸騰的音樂聲裏,鄭相宜試探地出手,把他拉到了房間中央——玻璃桌和牆壁之間。
“這個舞蹈作...是要踩鞋子嗎?”
鄭相宜瞬間松開了他的手,了手心的汗。
不會跳舞,之前拒絕陶斯曜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怕出錯。
可現在在夢裏。
鄭相宜擡頭瞥了眼他:“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我呀?”
陶時安沒意識到自己被倒打一耙,目一直落在的上,就連說話的時候也是歪著腦袋盯著。
“抱歉,我很…跳舞。我踩疼你了嗎?”
陶時安別扭地蹲下,小而窄的空間裏還怕到,長長腳被的子牢牢錮住了。
鄭相宜抿起,沒料到的是陶時安居然一手抓住的腳踝,往涼鞋的鞋尖看了看。
他不知道看了多久,突然仰起頭對說:
“沒有紅。”
這個角度看,他好像小狗。鄭相宜俯視著他,而他的目則毫不猶豫地黏在的臉上。
鄭相宜微微別過臉,還不習慣被人這樣注視著。
“還跳不跳啦?”往後走了幾步,正想著要不還是算了,“陶斯曜”卻朝出了手。
“我跳。”
鄭相宜聽了,頓時覺得自己的攻略計劃功了一半。
拉著他,學著網上看過的視頻,拉著他扭來扭去,可兩人的總會在各種角度相遇。
直到的手不小心到了某個邦邦的東西。
突然回手,遲疑地問:“你怎麽了?”
面前的男生眼可見地黑了臉。
Advertisement
夢也消失了。
——
淩晨兩點,陶時安從床上驚醒,他滿頭大汗,手指突然掀開被子,探向腰下。
指尖及到漉漉的一片時,陶時安呼吸一滯。
他到床邊的屜裏,屜被分了兩個區域,他從右側拿走一條換上,起帶著髒的那條離開了房間。
陶家有保姆負責清洗他和哥哥的,加上陶時安是全盲,本看不到任何東西,陶家就更不會讓他自己手洗服了。
原本他該把髒服都扔進垃圾簍裏,耐心等著家裏的阿姨過來收撿。
可是服被他的夢弄髒了。
他有些懊惱,不知所措地在腦中計算著去洗間的路徑。
陶時安記得阿姨說過,洗房在一樓廚房的左側,他倒是經常去廚房。
按照記憶中的路線,陶時安一路暢通無阻地走到了廚房門口。
這座別墅是專門為他買的,所有會讓他跌倒的障礙都不能有。
這也意味著這房子缺了生活氣息,陶斯曜只會在節假日回來住幾天。
現在,家裏只有他一個人。
他著牆壁走進一間房間,膝蓋直直地撞上了一個略微鋒利地東西。
他直接用將那東西踢開,繼續往前走。
哐當——
那東西發出了水聲。
陶時安停下腳步,蹲下索了一陣,發現它是個水桶。他一手將整桶水拎了起來,卻不知道要往哪裏倒。
他只能繼續在四周晃,不知道撞到了多東西。
突然間,他整個人和一個巨大的冰冷件重重地撞到了一起,因為力量不均,他直接往拎著水桶的那一邊倒去。
“撲通!”
他摔在了地上,逐漸覺得服越來越。
他仍固執地撐起,將自己手上的服狠狠扔到了地上。
沉默許久,他著氣爬起,一腦兒將服全都下來,慢慢走回了自己的房間,將睡和全都塞進髒簍中。
次日一早,陶家的保姆準時上班,陶時安讓把髒簍拿出去扔了。
保姆的聲音聽起來有些驚訝,但很快就答應了。踩著拖鞋下樓時會發出細微的響聲,陶時安很擅長分辨腳步聲。
他一路跟著走,直到聽到保姆滴的一聲打開了別墅的門,他才在門口晃悠了一下,接著往自己的房間走去。
他打開屏幕找到“某音”,點了兩下,進。仙提了下那個的昵稱,他記在了腦子裏。
“新關注我的。”
“小米蕉(上岸版)。”
“不想早八。”
…
他手指不停地往下,聲也就一遍遍念著的網名。
一個上午,他手腕都酸了,終于找到了仙說的那個,的昵稱是“夢中發財暴富錢來”。
他點開的聊天窗,從最新的一條消息開始聽。
“今天吃了超好吃的蛋包飯,親吻的貓臉。”他想了想,或許這個想表達自己吃完飯後還親了貓貓的臉,或者是看到了兩個貓貓正在臉。
他想不出來。
不過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腦中瞬間出現了兩個圓圈,疊在一起。
陶時安笑了一下,手指繼續往上。
“舍友不喜歡我,面帶眼淚的微笑。”
聽到這句話,他仿佛能到的眼淚。
這次,他聽到這些表不再是一頭霧水。表二字在他的世界裏也有了形狀。
他給對方發了條安的話,又第一次在表裏找到了“微笑”的表。
…
“嘟嘟。”
手機震了幾聲,鄭相宜低頭一看,抖音裏唯一的聯系人給發了消息。
他果然回關了。
時安:【蛋包飯很好吃呀!如果今天還會因為你的舍友生氣,那我請你吃蛋包飯。】
第二條消息是十個微笑的表。
鄭相宜心猛地一沉。
這表不是早就被認為是嘲諷了嗎?
想要問清楚時安的意思,下一秒就收到了一百塊的轉賬。
鄭相宜皺起眉頭,第一次懷疑對方的份。
給擾自己的陌生人轉賬,這行為不像是陶斯曜能做的。
解釋了幾句,到了晚上又聊起最近的瑣事。出乎意料的是,每一條對方都看了。
不知不覺,時安陪聊了很多天,突然給發了一張照片。
時安:【你知道這個小男孩長什麽樣子嗎?】
鄭相宜看了眼照片上的小男孩,他長得很好看,五和陶斯曜簡直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唯一中不足的是眼睛沒什麽神。
【很可的小孩,這是你小時候嗎】
鄭相宜已經習慣對方回複慢半拍了,起去扔了個垃圾,回來後就看到時安發了條消息。
【這是個盲人小孩,他今年剛滿十歲,想知道自己長什麽樣子。】
鄭相宜又點開那張照片,心中不免有些憾,思索片刻給他發去——
“他穿的是一件冷冷的服,很酷很酷。眉很濃,起來應該很溫暖也很紮人。彎彎的眼睛很可,他的長相讓人看了就很開心。”
“擁抱擁抱擁抱。”
文字和表的聲音一齊被他接收到了。陶時安想,對方一定也是個非常溫暖的人。
如果是小時候的他聽到這句話一定會想要抱的。
陶時安慢慢地彎起了角,繼續往前翻著消息,想要知道對方之前還給他發過什麽。
直到他聽到了——
“喜歡時安喜歡時安。”
“時安戴眼鏡好看。”
冰冷的系統聲一直無地念著“”字,陶時安的耳霎時紅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38 章
新婚嬌妻寵上癮
(桃花香)一場陰謀算計,她成為他的沖喜新娘,原以為是要嫁給一個糟老頭,沒想到新婚之夜,糟老頭秒變高顏值帥氣大總裁,腰不酸了,氣不喘了,夜夜春宵不早朝!「老婆,我們該生二胎了……」她怒而掀桌:「騙子!大騙子!說好的守寡放浪養小白臉呢?」——前半生所有的倒黴,都是為了積攢運氣遇到你。
245.9萬字8 30971 -
完結256 章

別和我撒嬌
痞帥浪子✖️乖軟甜妹,周景肆曾在數學書裏發現一封粉色的情書。 小姑娘字跡娟秀,筆畫間靦腆青澀,情書的內容很短,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 “今天見到你, 忽然很想帶你去可可西里看看海。” …… 溫紓這輩子做過兩件出格的事。 一是她年少時寫過一封情書,但沒署名。 二是暗戀周景肆六年,然後咬着牙復讀一年,考上跟他同一所大學。 她不聰明,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認識溫紓的人都說她性子內斂,漂亮是漂亮,卻如同冬日山間的一捧冰雪,溫和而疏冷。 只有周景肆知道,疏冷不過是她的保護色,少女膽怯又警惕,會在霧濛濛的清晨蹲在街邊喂學校的流浪貓。 他親眼目睹溫紓陷入夢魘時的恐懼無助。 見過她酒後抓着他衣袖,杏眼溼漉,難過的彷彿失去全世界。 少女眼睫輕顫着向他訴說情意,嗓音柔軟無助,哽咽的字不成句:“我、我回頭了,可他就是很好啊……” 他不好。 周景肆鬼使神差的想,原來是她。 一朝淪陷,無可救藥。 後來,他帶她去看“可可西里”的海,爲她單膝下跪,在少女眼眶微紅的注視下輕輕吻上她的無名指。 二十二歲清晨牽着她的手,去民政局蓋下豔紅的婚章。 #經年,她一眼望到盡頭,於此終得以窺見天光
45.4萬字8 21446 -
完結1693 章

離職后我懷了前上司的孩子
作為總裁首席秘書,衛顏一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號稱業界楷模。 然而卻一不小心,懷了上司的孩子! 為了保住崽崽,她故意作天作地,終于讓冷血魔王把自己給踹了! 正當她馬不停蹄,帶娃跑路時,魔王回過神來,又將她逮了回去! 衛顏,怒:“我辭職了!姑奶奶不伺候了!” 冷夜霆看看她,再看看她懷里的小奶團子:“那換我來伺候姑奶奶和小姑奶奶?”
165.2萬字8.18 38138 -
完結201 章

雙時空緝兇
【01】南牧很小的時候就遇到過一個人,這個人告訴他:絕對不要和溫秒成為朋友。 日長天久,在他快要忘記這件事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女生,那個女生叫做:溫秒。 【02】 比天才少女溫秒斬獲國內物理學最高獎項更令人震驚的是,她像小白鼠一樣被人殺害在生物科研室,連頭顱都被切開。
38萬字8 179 -
完結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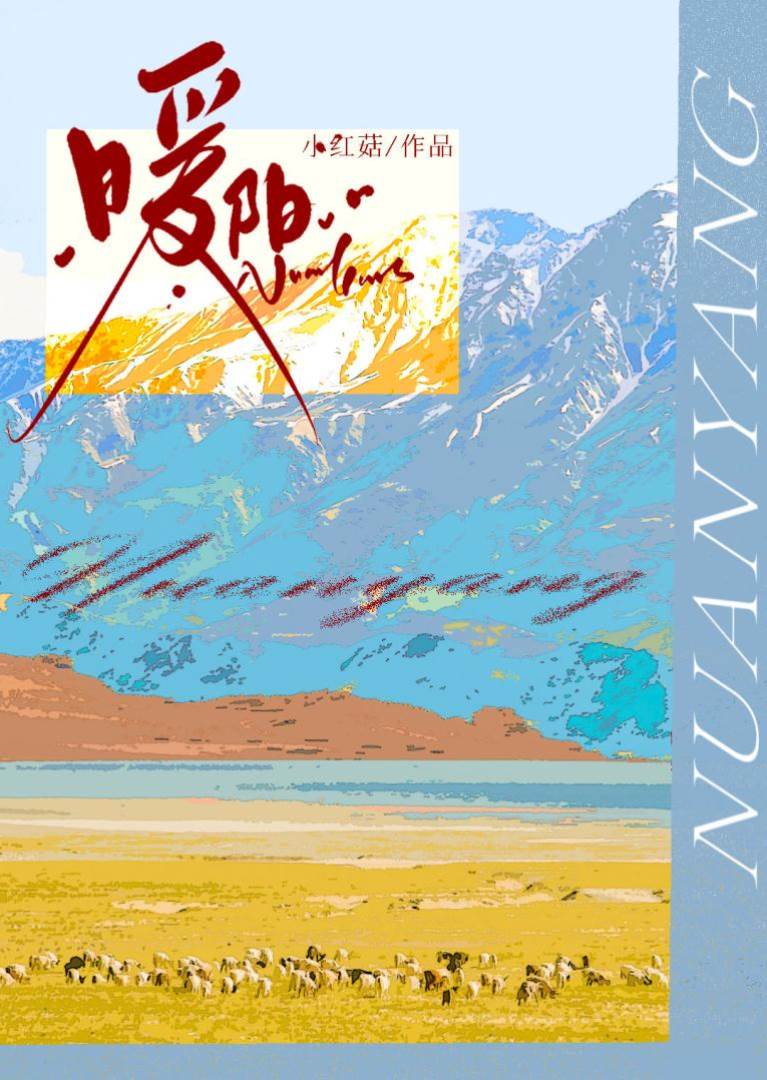
暖陽[先婚後愛]
文冉和丈夫是相親結婚,丈夫是個成熟穩重的人。 她一直以爲丈夫的感情是含蓄的,雖然他們結婚這麼久,他從來沒有說過愛,但是文冉覺得丈夫是愛她的。 他很溫柔,穩重,對她也很好,文冉覺得自己很幸福。 可是無意中發現的一本舊日記,上面是丈夫的字跡,卻讓她見識到了丈夫不一樣的個性。 原來他曾經也有個那麼喜歡的人,也曾熱情陽光。 她曾經還暗自竊喜,那麼優秀的丈夫與平凡普通的她在一起,肯定是被她吸引。 現在她卻無法肯定,也許僅僅只是因爲合適罷了。 放手可能是她最好的選擇。 *** 我的妻子好像有祕密,但是她不想讓我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他有點緊張,總覺得她好像在密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卻無法探尋。 有一天 妻子只留下了一封信,說她想要出去走走,張宇桉卻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哪裏做得不夠好,讓她輕易地將他拋下。 張宇桉現在只想讓她快些回來,讓他能好好愛她! *** 小吳護士: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段時間張醫生不正常。 小王護士:對,他以前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發朋友圈的,現在每隔幾天我都能看到他發的朋友圈。 小吳護士:今天他還發了自己一臉滄桑在門診部看診的照片,完全不像以前的他。 小劉護士:這你們就不知道了吧,張醫生在暗搓搓賣慘,應該是想要勾起某個人的同情。 小王護士:難道是小文姐?聽說小文姐出去旅遊了,一直還沒回來。 小劉護士:肯定是,男人總是這樣的,得到了不珍惜,失去了纔會追悔莫及。
22.5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