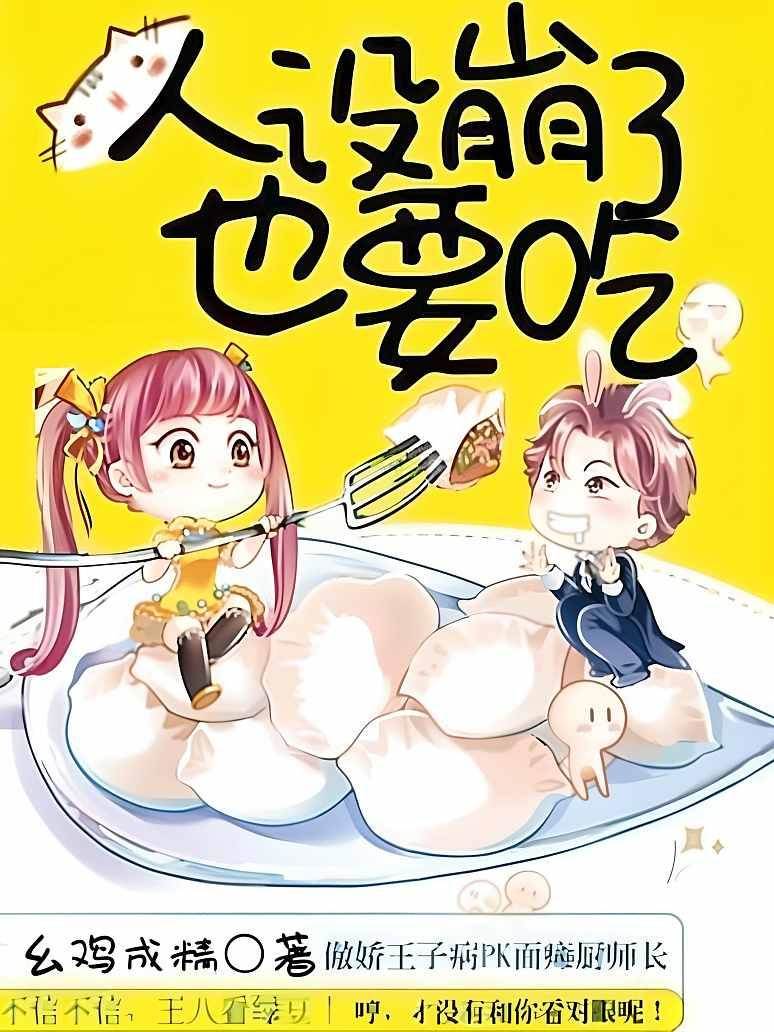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南風霧裡》 第15頁
前幾天的一場雨把夏日的焦躁驅趕得所剩無幾,陳粥在昏沉的樹葉間隙落里看著窗外的風景。拿起沈方易給的相機,想記錄窗外那些轉瞬即逝的景,舉起相機的那刻,又緩緩放下。
沈方易從路程的小憩中醒來看到的,就是這一幕。
坐在靠窗獨立座椅上的小姑娘,手裡攥著那臺拍立得,雙規矩地踩在車裡的羊墊子上,腳尖並在一起,朝向背離他的那個方向,直直地看著窗外。
沈方易用腳尖輕輕地了的腳後跟,微微垂著頭問,「在看什麼?」
白的板鞋上面是一個白的創口,隨著的轉,經過外頭毫無遮擋的馬路時,晃過來一道刺眼的白。
「風景。」陳粥指著窗外,真心地說到:「特別的風景。」
車子開在林的彎道上,從窗戶外面看去,能看到盤旋在山腳下的一條河流,野生的各的山花點綴在如雲一樣縹緲的河流。
眼睛裡的餘過著外面的山川河流:「我要把他們都記在腦子裡。」
沈方易回過神來,指了指手裡的相機,「你可以把他們拍下來。」
陳粥搖搖頭:「相紙有限,拍一張就一張了。」
沈方易那一刻有半秒的語塞,他知道語塞和沉默算不上是一種紳士的行為,其實他可以說,怕什麼,沒了再買。
但是恰恰在那一刻,不知道為什麼一句如此平常的安會顯得有些殘忍,他只得作罷,什麼都沒有說,讓這種不紳士的沉默充斥著整個車廂。
Advertisement
一個算不上遊刃有餘的剎車打破這陣沉默。
陳粥覺到車子震了一下,連忙抓手中的拍立得,等車子停下來了,長脖子往外看去,是不是撞上了什麼東西?
蔣契差點從后座滾下來,他了撞疼的頭,罵罵咧咧起來,「老王,你怎麼開的車?」
「不好意思蔣,剛剛經過的地方有坍塌,我打了一圈方向盤,結果遇到了個什麼堅的東西,像是塊大石頭,現在作臺顯示的是車胎破了。
「什麼?你怎麼開車的,有坍塌的地方你不能早點看到嗎?這荒郊野嶺的車胎破了你是要我們一群人留在這兒餵狼嗎?」
「行了蔣契。」沈方易阻止蔣契,起走到駕駛室的後面,自己問著司機,「車胎還能堅持多久?」
「沈先生,抱歉,只能堅持五里。」
沈方易回頭對蔣契說到:「讓人就近再送輛車過來。」
而後,他微微彎腰,在顯示屏附近的一個地方點了點,「我們先去那裡。」
說完之後,他過來,陳粥急忙問道,「怎麼了,是車子壞了嗎?」
他寬到:「問題不大,我們先去附近的地方歇歇腳。」
這返程被一個小意外打破,幾個人只能先去附近找個地方休息一下,等沈方易的人把車送來。
附近有一個自然樸素的小村子。
村子裡里外外種滿了比人還高的甘蔗,住在這兒的人以研製紅糖為生,沈方易他們去找人修車了,陳粥在村口,無聊地看那老師傅曬糖。
Advertisement
村口圍繞著一群小朋友,被強日曬曬的臉黑撲撲的,腳上的鞋子上還沾著從地里幫忙抬甘蔗的泥土,幾個人圍坐在一起,手上拿了本掉了幾張頁面的西遊記。
原本看得好好的,沒過多久不知道為了什麼事吵起來。
幾個孩子站在兩撥,一撥說著二郎神君厲害,一撥說著最厲害的還是齊天大聖,誰也說不過誰,扭打在一塊。
陳粥站在下風口,吃了一臉灰塵,走過去,撿起那本他們丟在地上的帶著圖畫的本子,「好了好了,別打了,你們說的都對,兩人打平了。」
那群孩子一聽這話,停下作,問,「你怎麼知道?」
陳粥聳聳肩,「我看過啊。」
「真的?」
「真的,孫悟空很厲害,二郎神也很厲害,不過孫悟空再厲害後來也被如來佛祖在五指山下了。」
陳粥這話一說,對面的孩子立刻變了臉,其中一個囂到:「我不信!真的有人比孫悟空還要厲害?」
陳粥:「我騙你幹什麼。」
蹲下來,拿過那本破損的書,翻了翻,「這裡缺了幾頁,我給你們講講吧。」
「好啊好啊!」
……
沈方易回來的時候,陳粥被一群野孩子圍在中間。
蹲在樹蔭的泥地上,手裡拿了樹杈子,在地上畫來畫去的。
小朋友托著腮幫子,一臉求知,說的眉飛起舞的,從三打白骨說到真假猴王。
不過沒多久,抬頭看到他,撣了撣自己的手,站起來,頗有儀式地跟那幫孩子說到,「好了,我們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啦!」
Advertisement
蹲在地上的小朋友連連拍手,滿眼都是星星,「姐姐你好厲害啊,你是大學生吧!」
陳粥一愣,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沒什麼,就是西遊記,你們看看電視就知道了。」
「我們沒有電視。」其中一個小朋友搖搖頭。
陳粥心中微微驚訝,家境不算富裕,但陳學閔從小到大幾乎沒有讓在生活上吃過什麼苦,忘了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不擁有平等的機會。
「你跟我們老師一樣博學,我們老師就是個大學生,他跟我們說,只要我們好好學習,就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77 章
豪門梟寵:重生小妻兇兇噠
重生前安夏對韓穆宸恨之入骨。重生後的安夏,每天都在炫男朋友!遇到追求者,安夏:「我男朋友很帥,沒有要換男朋友的想法。」遇到屌絲,安夏:「我男朋友很有錢,能砸死你的那種哦~」眾人對安夏的男朋友很好奇,帥能帥的過帝都韓家大少韓穆宸?豪能豪過L.K的總裁?某天一名戶名為韓穆宸的藍V發了一條官微,艾特了一個使用者名稱為是安夏呀的黃V,內容是:「老婆求名分。」好奇安夏男朋友的那些人:好大一個甜瓜!這不就是韓大少L.K本尊嗎?!2G吃瓜群眾:不好意思,剛出村!乞討大隊隊長:妹子你孩子還要不要?眾人:孩子都有了?giao!
86.2萬字8 41041 -
完結111 章

誰能不愛綠茶呢
陳嫵愛了天之驕子許溯七年,最終成為他的妻子。朋友祝她得償所愿,守得云開見月明。但是在結婚的第三年,許溯的初戀回來了,他瞞著她為初戀打理好一切,甚至趁她睡著,去酒吧接喝醉的初戀。哪怕許溯仍然對她百般示好,但陳嫵清醒地知道,這不是她想要的。…
31.8萬字8.18 57478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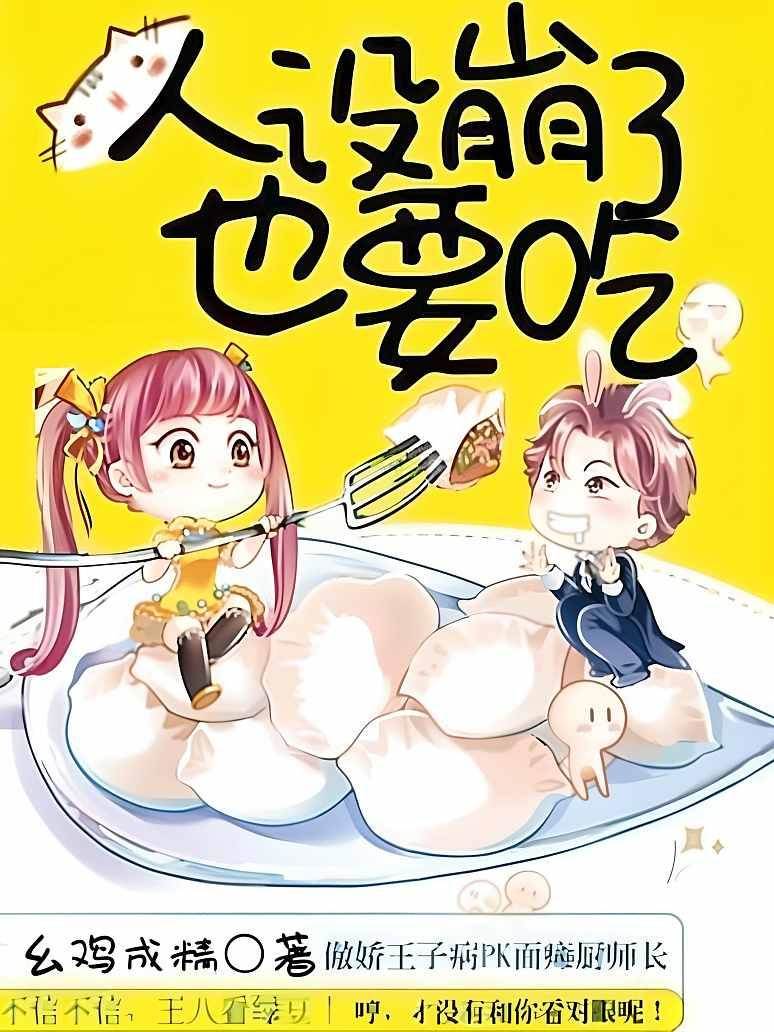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
完結166 章

聲聲慕我
岑聲聲最無助時,是靳逸琛拉她出泥潭。 她以爲找到真愛,哪怕被嘲不配,她也滿心滿眼都是他。 只是他的手,當初能給她,而後也能給別人。 生日那天,她等了靳逸琛一整晚,而他在忙着做別個女孩的Superman。 —— 某次聚會,岑聲聲跟着靳逸琛,第一次見到了周時慕。 男人半長碎髮遮住凌厲眉目,冷白修長的指骨捏着把牌,鬆鬆垮垮地坐在那,卻平添迫人的氣勢。 曾嘲她不配的女人藉着敬酒的由頭不死心地往周時慕身上貼。 一直冷臉寡言的男人不勝其煩。 靳逸琛突然心血來潮也讓岑聲聲去敬酒。 周遭先一愣,而後突然開始起鬨。 周時慕淡漠地擡眸,目光掃過她輕顫的長睫,“想要什麼?” 她沒懂,以爲是問她敬酒詞,顫聲道:“諸事皆順。” —— 在一起時靳逸琛從未珍惜,後來分手,他又瘋魔般念着岑聲聲的好。 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岑聲聲不堪其擾,連夜搬家, 那天夜路蕭瑟,風雪呼號,周時慕攔住她的去路,邀她上車, “不是要諸事皆順嗎?” “找我就行。” —— 後來,圈子裏再組聚會,總是邀不到周時慕, 一次,偶聽說他在隔壁包間,衆人齊齊急着過去, 卻見那個平素冷麪不可一世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摟着懷裏的小姑娘,笑得慵懶恣意, “聲聲乖,快許願。” “什麼我都能幫你實現。”
25.7萬字8 1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