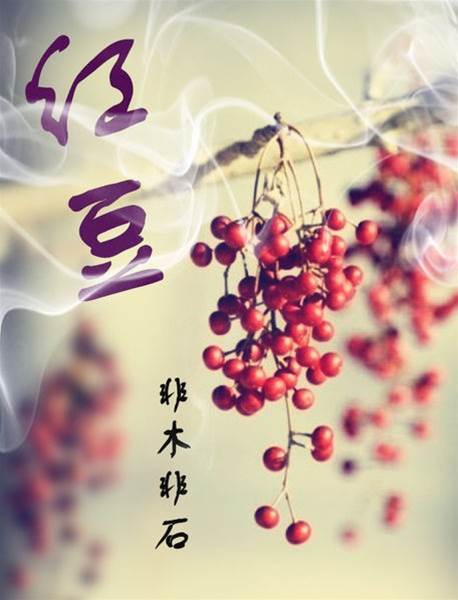《回到反派黑化前》 19、破局(一)
第19章
小雨瀝瀝,湫十和宋昀訶一前一后回到主城府。
湫十惦記著跡圖上那個缺了一半的字,轉去了主城府的藏書閣,宋昀訶則回了議政殿的書房理剩下的一堆爛攤子。
藏書閣在主城府的側南方,占地不小,上下共四層,下面兩層是數以萬計的妖族科普、習、種族特征等,出有專門的守衛登記,上面兩層收藏的則是一些從遠古傳下來的奇聞異志,珍貴史錄,尋常人不得進,有長老日夜值守。
湫十喜歡研究這些,白棠院里也有一座書屋,但論藏書數量比不過這座,有些珍貴的孤本只存在藏書閣里,所以第一時間就帶著跡圖來了這里。
是藏書閣的常客了,今日守著通往第三層口的是一名長老的關門弟子,見了湫十急忙行禮,沒有多問,只留了一道神識氣息就讓進去了。
主城府上有資格進藏書閣三四層的,連著長老們一起,都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因而湫十進去的時候,偌大的第三層并沒有人,冷冷清清的,四邊的角落里點著不滅的靈燈,空氣中彌漫著一古本的陳年松香味。
十幾個巨大的木制書柜佇立,浩如煙海的書籍在這里安靜陳列,湫十輕車路地走到最后面兩排書架前,指尖點在一本古書的書脊上,稍稍一用力,就將那本書了出來。
目是一些繁瑣而復雜的圖形字樣,并不是現今六界通用的文字,湫十看扉頁上的十幾行小字都有些吃力,得一個字一個字辨認,拼湊,再從腦中里組合一句通暢的話。
藏書閣的書實在是太多了,若是一本一本翻下去,在鹿原境開啟之前,可能都看不完一半。
Advertisement
所以湫十只看扉頁上的那段文字,最多看完第一頁,覺得不是自己要找的就立刻換下一本。
即使如此,沒過多久,的眼還是花了。
倚在書柜的邊角上,一只手捧著書,一只手點在眉心,著自己往下看。
這種時候,兩個時辰似乎過得格外快,轉瞬即逝。
湫十再一次擰著眉將手中的書放回原的時候,腰間系著的留音玉閃爍了幾下,發燙,泛出溫潤的。
湫十手指尖微不可見地蜷了蜷,一點靈力躥進留音玉里,應到里面那道氣息后,原本靠在書柜邊的脊背直了些,黑白分明的目里閃過詫異的神。
秦冬霖上的劍意實在是太有標志了,本無需仔細分辨就知道是他。
從前,兩人聯系,十次有九次半是湫十主找的他,剩下半次還多半是他實在被煩得不行了,遭不住才回了,這次程翌的事發生后,就更不用多說,他直到現在都沒給什麼好臉,湫十用留音玉聯系他,他直接就當沒這麼個人。
秦冬霖是個妥妥的修煉狂魔,留音玉這種東西在他眼里礙事得不行,要不是湫十耳提面命很多次,他上本不會出現這種東西。
這回破天荒聯系,肯定有重要的事。
湫十取下留音玉,見那邊沒有聲音,試探地從嚨里嗯的一聲,小聲喊:“秦冬霖?”
“是我。”這一次,流暢而冷然的聲線清晰地傳到湫十的耳朵里,秦冬霖言簡意賅:“你人在哪?”
“我?”湫十反應過來,一雙脈脈淚眸在眼前的書柜上掃了一圈,有些頭疼地摁了摁太,道:“在主城的藏書閣里待著,翻了半天的遠古史籍,提到過鹿原境的都對不上。”
Advertisement
“一刻鐘后。”秦冬霖突然來了這麼一句:“我上去。”
沒等湫十回味過來,手掌心里躺著的留音玉已經沒有靜了。
白棠院外,明月看著不遠拔如青竹的男子背影,僵得跟石頭一樣。
秦冬霖難得穿了一白,人如陌上玉,肩窄腰痩,蕭蕭肅肅,人站在那,便自然而然的為了天地間的一柄劍。
妖族重脈,高位者的威對低位者來說,無異于了一座大山在兩邊肩膀上。
明月都在打。
秦冬霖不常來主城府,作為流岐山的君,他每天要忙的事絕對不比宋昀訶,該接手的一樣也逃不過,同時還得兼顧修煉,一天恨不得掰兩天來過,見了湫十就頭疼,主現到跟前這種事,本不可能。
秦冬霖悄無聲息出現在白棠院院門口,明月將他往里迎,他淡漠地搖了下頭,目凝著,落向西南方。
明月順著他的目一,眼瞳微微一凝,不敢言語。
那是已經被夷為平地,這幾日正在重修的東蘅院。
脈低微者覺不到殘留著空氣中的極淡的一氣息,秦冬霖卻能清楚的捕捉到。
那條黑龍的氣息,宛若跗骨之蛆一般纏繞在附近,久久不散。
半晌,秦冬霖瘦削分明,寡白的長指不不慢抬起,點至半空,一無形的氣浪將他的衫袖擺吹得起。
須臾,他收回手指,一步踏出,轉朝著藏書閣的方向去了。
明月怔然松了一口氣,肩膀往下了,再看西南方的時候,到的是跟之前截然不同的氣息,那氣息純正,醇和,充著皇族的威,將之前殘留的那雪一樣清冽干凈的氣息徹底碾散。
Advertisement
秦冬霖作為流岐山的君主,主城唯一一位小公主的未來夫婿,在出示了份令牌后,在主城府一路暢通,不到一刻鐘,就進了藏書閣的第三層。
他的腳步聲很輕,在廣闊而清冷的藏書閣中像一片輕飄飄的落葉,沒有驚起半分靜。
湫十換了張書柜靠著,長長的擺在雪白的腳踝上輕掃,蜻蜓點水一樣稍即離,天鵝般的長頸微折,烏黑的長發垂下來,落到手中捧著的書頁上。
安靜又溫婉,看著很乖。
每次只要專注著做一件事,不開口說話時,秦冬霖總會有種錯覺,覺得仿佛就是這樣,優雅端莊,大方自然,跟那面那些世族貴一樣。不會像小一樣哼哼唧唧纏得人不開,不會為了一件寶貝磨磨蹭蹭在他邊念叨許久。
然而,一開口,這種嫻靜的氛圍便如泡沫一樣,一就破——
“來了?”湫十察覺到邊的靜,視線從手中的書冊轉到秦冬霖那張好看的俊臉上,輕輕眨了眨眼,往他后瞅了瞅,很輕地“咦”了一聲,語氣輕快地問:“伍斐呢?被你甩下了?”
秦冬霖不置可否,目落在手中的古籍上,眉骨微抬,問:“看的什麼書?”
“遠古時期的一些戰史。”湫十將書合上,十纖細的手指落在舊黃的扉頁上,被襯得生生,青蔥一樣,給人一種將折就斷的錯覺。
“怎麼突然來了?”湫十問。
“不是跟你說了,往遠古之前,洪荒時期查?”秦冬霖向來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突然來主城府,肯定是有事。
知道他來之后,湫十就猜到他是因為什麼事來的。
“等著。”湫十將手里的書往他手掌上一放,轉去了最后一排書柜,沒過多久,抱著三四本古籍回來,將它們堆到秦冬霖懷里,下抬高了些,道:“整個藏書閣,就這四本提到了洪荒,你自己看。”
Advertisement
秦冬霖捻起其中一本,隨意翻開一頁,深邃的目凝了一瞬。
“站著說話不腰疼說的就是你。”湫十拿眼瞅他,手指往書頁上隨意指了指,“翻到了有什麼用,本看不懂。”
“你看得懂的話,就換你來看。”湫十抱怨似地小聲嘟囔:“是遠古的這些,我辨認起來都十分費勁,洪荒神語晦古怪,許多字符已經不可考據,我看得腦袋疼。”
洪荒是最神的時期,許多六界不解之謎都藏匿在那個時代,中洲的覆滅,妖帝的隕落,大陸的分裂,通通都覆蓋著一層云,許多事件,到現在也沒個的說法,而這種神,甚至也現在了文字上。
扭曲得像蛇群盤踞,如雜的藤蔓纏的字符或間隔很大,或排得麻麻,一眼掃下來,跟鬼畫符沒什麼差別。
湫十手召來一張小凳,再從空間戒里翻出那塊跡圖將它平平整整攤上去,除卻中間被斬開的那一團像個字,其他的黑線簡直像是一朵朵開得詭異的魔花。
“對著這個字找找看,把有可能符合的都記下來。”湫十歪頭,與秦冬霖對視片刻,道:“要是真能查出來,等鹿原境一開,我們就直接帶人去跡圖標注的位置,把里面的東西一鍋端,連棵草都不給他們留。”
湫十的格,很大一部分,跟秦冬霖長年累月的潛移默化有關。
所以說的這些話,秦冬霖覺得完全沒問題。
他本來就是這樣想的。
接下來的三個半時辰,從傍晚到深夜,兩人凝著眉看著書,時不時瞅一眼圖上的字對比。
看到最后,湫十索將書一合,頓了頓,認真地提議:“鹿原境中,各族弟子生死由天,不論發生何事,各族各界不得干預。我們要不提前部署一下,一進去就將他們的圖搶過來?”
秦冬霖從善如流地跟著摁下自己手里的古籍,一直皺著的眉松了松,他道:“也不是不行。”
說完,他像是終于記起來什麼,慢條斯理地道:“對了,那條救過你的黑龍,在今日晌午,也救了莫一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八零萬元戶家的嬌軟小女兒
平靜的軍屬大院裡,忽然搬來了一家“萬元戶”,這對於大院的各家各戶來說都是個新鮮事。 這家的男主人頭戴金項鍊,手戴鑲金表,見誰都勾肩搭背,笑容可掬地遞上一支紅塔山,稱兄道弟; 這家的女主人風風火火、聰明能幹,見人三分笑,不過一周的時間就跟各家女眷親如姐妹; 這家的兒子帥氣又爽朗,籃球技術高超,很快就隱隱要成為大院男孩中的扛把子,女孩們的心尖子。 這家的小女兒……誒?這家還有個女兒? …… 直到“萬元戶”家搬進來大半個月後,大院鄰里們才知道,他們家居然還有個嬌滴滴的小女兒。 大傢伙都很納悶,這家的小姑娘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也不愛玩也不愛交朋友,這到底像誰? 不像他們老謝家的基因能生出來的啊。 直到院裡搞文藝演出,小姑娘被趕鴨子上架,一曲《昭君出塞》迷得整個大院的大小伙小男娃神魂顛倒。 也不知道是被琴迷的,還是被人迷的。 不過不好的地方也有,一朝出風頭,這又美又嬌的小姑娘就被院裡知名的霸王惦記上了。 ----------- 歐陽軒性子混,路子野,用寧城話說,就是“邪性得很”。 軍屬大院周圍一條街,他的大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總結來說就是——見了他得繞道走。 唯獨那個會彈琴的“小昭君”不怕他。 歐陽軒覺得有點意思,忍不住想逮著人欺負欺負。 不過喜歡小昭君的人有點多,經常欺負不著。 於是他找到他那個一直為他頭禿的爹,頭一次坐下來跟他平心靜氣地談判。 “爸,我要把謝家那個小女兒娶回家,留給你的時間不多,你可以盡快去準備準備了。” 冤種爹:“……?” ----------------------------------------- 婚前拽哥霸王婚後寵妻狂魔男主X 嬌軟社恐鈍感阿宅女主 女主團寵萬人迷,男主未來大佬 成年前沒有任何感情和親熱描寫 【排雷排雷排雷排雷】: 1)女主前期性格社恐膽小慫,依賴家人,一點兒也不強大,後期才會慢慢成長,介意的請勿點 2)男主初登場的時候比較招人煩,喜歡上女主以後才越來越好,介意的可以罵他,別罵我 家長里短治愈風年代文,搞對象為主,男女主事業和成長為輔,沒什麼奇葩極品,節奏較慢
22.8萬字8.15 9871 -
完結12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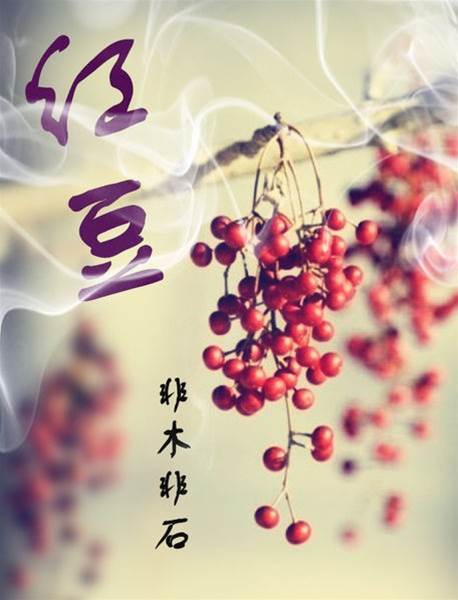
紅豆
他捏著手機慢慢把玩,似笑非笑說:“看,你守著我落兩滴淚,我心疼了,什麼不能給你?”
30.6萬字8 8179 -
完結178 章

天終于落雨
二十五歲那年,季檬前男友劈腿,她頭頂催婚壓力,破罐破摔,去找小時候住她鄰居家的沈鶴霄閃婚,假裝夫妻。 意料之外,他答應了。 沈鶴霄,現在是蘇城大學最年輕的天文系副教授。 為人極其清冷寡言,長相俊美,對任何人都冷若冰霜,堪稱無人能摘的高嶺之花。 兩人領證后,眾人議論紛紛。 都說他們哪哪都不般配,完全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這婚姻也注定長久不了。 甚至有大膽的學生跟季檬玩笑著問:“沈教授在家,是不是也像個大冰塊兒?” 季檬心不在焉地點點頭,隨口道:“啊,差不多吧。” 于是,這句話一傳十,十傳百,最后傳到沈鶴霄耳中,已經變成: [沈教授和太太感情不和,可能快離婚了。] - 沒想到幾個月后,數百人的視頻課上,中場休息,沈教授“忘了”關麥。 安靜的網絡會議室,突然傳來嬌滴滴的女聲。 “老公,你什麼時候下課啊,說好這盒櫻桃你要喂我吃——” 沈鶴霄的嗓音低沉又寵溺:“乖,很快的。現在課間,可以先過來抱抱。” 霎時間,討論界面噌噌噌刷起了問號,各大群聊也爆了。 -之前誰說的感情不和? -沈教授平時在家都是這麼說話的? -這還是我認識的沈教授嗎? * 季檬原本也以為,這場婚姻只是為了迎合世俗的一場表演,注定貌合神離。 直到某日,她意外發現了沈鶴霄十六歲的日記本。 上面每一頁的內容,都與她有關。 「漫成無船的渡口,雨空自迷茫。」 「而我,終在雨里等你。」
24.7萬字8.18 228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