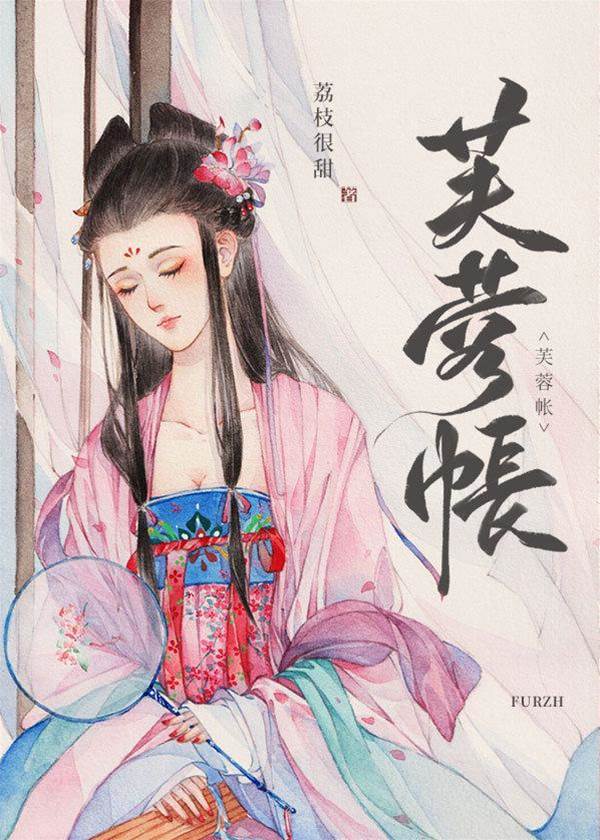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嗣兄》 試探
從許長安的角度,一眼就能看到他神異樣,耳通紅。或許他自己都沒注意到,他站在那裡,看著都有些僵。
角微勾,心想看來吳富貴說的,還真有幾分道理。
微一凝神,承志理了理思緒,輕聲問:「我聽說你病了,特來看看。你……還好吧?」
到這個時候,他才敢抬眸看,又不能平視,只能目視前方的同時眼瞼下垂。
許長安輕笑一聲,學著表妹的模樣,語說道:「我被你推進水裡,裳都了,還生了病,你說我好不好?」
承志怔了一瞬,他來許家已有一些時日了,跟這個「妹妹」也有過幾次接。可每每見了他,都是神冰冷、語氣厭惡,彷彿看他一眼都嫌髒了眼睛,只差沒把「討厭」兩個字寫在臉上。
他承認,他希能跟他親近和睦一些。
可第一次聽到用這種類似於撒賣乖的語氣跟他說話,他只覺得一個激靈,頭皮陣陣發麻。
他只得出聲道歉:「對不起,我當時不是故意,是我……」
一說起昨日之事,承志難免又想起就湊在他面前,似笑非笑,吐氣如蘭:「……總該不會是喜歡我吧?」
雙目微闔,他深吸一口氣,盡量讓自己平靜下來:「昨日之事著實是我不對,以後不會再這樣了。我聽聞發熱之人,大多食不振,所以回來的路上,買了一些山楂餞兒,你嘗嘗。」
承志說著取出一個油紙包,此時也不知道該遞給誰,乾脆往旁邊走了幾步,小心放在桌上。
「山楂雖好,可發熱之人不宜多吃。不過你有這份心,也算是難得了。」許長安話一出口,才意識到似乎過於冷了一些。不像是對待未來夫婿,倒像是對新來的下屬。
Advertisement
想著表妹素日與說話的模樣,偏著頭,輕聲問:「你把我推下水,害我生了病,這一包餞就想打發我啊?」
輕輕,帶著的虛弱,讓人不由頓生憐惜之意。
承志心裡的愧疚之更濃了,幾乎是口而出:「那你想要我做些什麼?」
「我想有什麼用啊?我想了你就會去做嗎?」許長安笑盈盈看著,清亮的眼眸里彷彿有流的。
承志當即鄭重表示:「只要你想,只要我能做到。」
「行。」許長安也不跟他繞彎子了,下意識坐直了,「那你嫁給我吧!」
此言一出,承志瞬間瞳孔微,神劇變:「你說什麼?」
他想他肯定是出現幻覺了,或者是他本就在做夢。怎麼會笑地跟他說話?還向他提出一個荒唐的請求?
而正端茶過來的青黛更是手腕一抖,茶碗落地摔了個碎,角沾染了點點茶漬。
許長安聽到靜,一把掀開蓋在上的薄被,焦急問:「怎麼樣,青黛?有沒有燙傷?」
說著就要穿鞋上前去查看。
青黛連忙應聲:「沒有,沒有燙傷,只是污了子。」
拍了拍怦怦直跳的口,老天爺啊,聽到了什麼?
知道沒事,許長安鬆一口氣。不過有了這麼一個變故,也不再重新回到床榻上了,而是乾脆轉到承志面前:「我方才所說之事,你覺得怎麼樣啊?」
而這短短的數息之間,承志心裡已浮現過諸多念頭。
他搖一搖頭,認真拒絕:「你我兄妹,怎麼能提嫁娶之事?這種玩笑,以後萬萬不要再提了。再者,我是男子,我怎麼能嫁……嫁給你?」
「誰說男子不能嫁?贅就可以啊。」許長安理直氣壯,「至於兄妹,我娘可只生了我一個。只要你一天不嗣許家,我們就一天算不得兄妹。」
Advertisement
想了想,輕輕咬一咬,微微仰著頭看他,聲音極輕:「你,真的一點都不喜歡我麼?」
兩人離得很近,只穿了一煙灰寢,衫寬大,顯得整個人格外纖瘦脆弱。
承志覺自己的心似乎被一隻手給攥住,不由地就想起那天在金葯堂的模樣。
他線抿,眼眸垂下,不與對視:「你,你好好養病,不要再說了。今天的話,我就當沒有聽到。我,我走了。」
承志哪敢再待?他胡拱一拱手,轉疾走,頗有些落荒而逃的架勢。
而許長安輕嘖一聲,心想:這讓一個男人心甘願嫁給自己,好像也不是件容易事兒。
青黛收拾了殘局換過后回來,見小姐只穿著寢,腳踩著鞋子站在房。
將茶盞放下,輕聲問:「小姐,您剛才都在說什麼啊?是不是燒糊塗了?怎麼說出那麼一番話來?他都把你推下水了,你還想著嫁給他?」
許長安糾正:「不是嫁給他,是讓他嫁給我。他嫁給我,就沒法做我爹的兒子了。」
或許也不必真的招他為婿,只需要他能心甘願放棄做許家的嗣子就行。
青黛愣了愣神,一時竟不知該作何反應,好一會兒才道:「可是,他怎麼可能願意贅啊?」
誰會放著爺不做而去做個贅婿呢?
「所以,我就是在想辦法讓他願意啊。」許長安笑了笑,「青黛,你等會兒去瞧瞧,看錶小姐忙不忙。」
自小做男子慣了,有的事,可能還真的需要向真正的姑娘家學習。
「是。」青黛答應下來。
承志離了青松園,一路行得極快。還未到書房,就到信步走來的義父。
許敬業雙手負后,饒有興緻地問:「你走這麼快做什麼?後面有人拿子追你啊?」
Advertisement
承志停步行禮:「義父。」
向他後看了看,許敬業問:「我聽下人說,你一回來就去看長安了?」
他不提還好,這麼一提,承志不由一陣心虛:「是,我聽說病了,帶了一些東西給。」
「嗯,是該這樣。」許敬業點一點頭,「雖然你不是我親生的,可以後你們就跟親兄妹沒什麼分別。子怪,可能有時候說話不中聽。你這做大哥的,就多擔待。」
「是,我知道。」承志應著,又忍不住問,「義父,我聽說以前金葯堂是由,由妹妹打理的。既是如此,何不為招贅一個夫婿,繼續由掌管?」
許敬業眼睛微瞇,狐疑地問:「是不是長安跟你說了什麼?」
承志心中一凜,連忙否認:「沒有,沒跟我說話。我是今天在藥鋪聽見他們說起一些事,心裡好奇,所以……」
「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嗎?許家百年規矩,金葯堂傳子不傳,傳兒不傳婿。就算招贅了,我也得再過繼一個嗣子。到時候兩方爭相起來,只怕家宅不寧。」許敬業擺一擺手,語重心長,「你放心,現在也就鬧鬧脾氣,許家遲早還是要到你手裡的,你可千萬不要辜負我對你的期待啊。」
承志鄭重點頭:「義父放心,義父的大恩,承志永遠不會忘記。」
「算了,不說這些了。你辛苦一天,只怕也累了,早些休息吧。」
「是。」承志施了一禮,告辭離去。
不知道為什麼,跟義父談了幾句,他心裡竟湧上若有若無的失落。
夜幕漸漸降臨。
青松園的燭火亮了。
「表哥,你是不是病的很重啊?」陳茵茵睫羽,眼眶裡很快蘊滿了淚水,「你以前生病都不跟我說,都是瞞著我的。」
Advertisement
——雖然知道了這是表姐,但一著急,還是會不控制地喊「表哥」。
許長安含笑看著:「我沒事,喝過葯,上不燙了。我請你過來,是想向你請教一些事。」
「你能請教我什麼啊?我什麼都不會啊。」陳茵茵不解。
許長安笑笑:「不不不,這些你都會的。就是問些裳首飾、荷包香囊這一類兒家的東西。」
「啊,你說這個啊,你說這個我擅長。」陳茵茵來了興緻,上下打量著表姐,「首先呢,咱們就來說裳。其實吧,我覺得你穿什麼裳都好看。你以前穿男裝穿慣了,你要真穿上鮮艷子,我可能還不習慣……」
許長安笑聽著,時不時地遞上一杯茶水,又請吃餞兒。
陳茵茵看見餞,心中微訝:「原來表哥也吃零啊。」
許長安笑笑:「這有什麼奇怪的?我也是人啊。」
只不過這餞兒不是買的罷了。
買餞的人這會兒正自心煩意。
這些天承志白天在金葯堂幫忙學習,晚上在書房看醫書。他記憶很,雜念也。所以看書時全神貫注,很分神。
但今天晚上,他卻莫名地到煩躁,半個時辰過去,竟只看了一頁。
他合上雙目,默默告誡自己:靜下心來,認真學醫。你答應了義父,不可辜負他的期待。
再睜開眼時,他眸中一片清明。
※※※※※※※※※※※※※※※※※※※※
麼麼噠
糾結癥晚期,可能需要抓個鬮謝在2021-04-0321:48:06~2021-04-0422:04:57期間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哦~
謝灌溉營養的小天使:貳貳叄1瓶;
非常謝大家對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19 章
腹黑世子妃日常
一朝穿越,腹黑狡詐的她竟成身中寒毒的病弱千金,未婚夫唯利是圖,將她貶為賤妾,她冷冷一笑,勇退婚,甩渣男,嫁世子,亮瞎了滿朝文武的眼。 不過,世子,說好的隻是合作算計人,你怎麼假戲真做了?喂喂,別說話不算話啊。
39.1萬字7.75 70010 -
完結652 章

重生之嫡女毒妃
枕邊之人背叛,身邊之人捅刀,她的一生,皆是陰謀算計。 一朝重生,她仰天狂笑! 前世欺我辱我害我之人,這一世,我顧蘭若必將你們狠狠踩在腳下,絕不重蹈覆轍! 什麼,傳言她囂張跋扈,目中無人,琴棋書畫,樣樣都瞎?呸! 待她一身紅衣驚艷世人之時,世人皆嘆,「謠言可謂啊」 這一世,仇人的命,要取的! 夫君的大腿,要抱的! 等等,她只是想抱個大腿啊喂,夫君你別過來!
113.7萬字8 25279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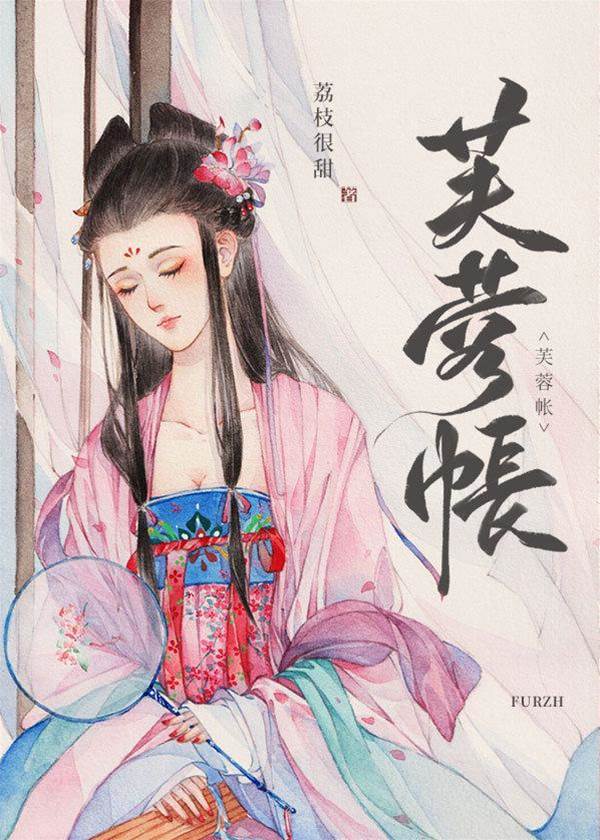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626 章

妃你莫屬:王妃,請低調
作為軍事大學的高材生,安汐無比嫌棄自己那個四肢不勤,白長一張好皮囊的弟弟安毅。可一朝不慎穿越,那傻弟弟竟然翻身做了王爺,而她卻成了那位王爺的貼身侍女;自小建立的權威受到挑戰,安汐決定重振威信。所以在諾大的王府內經常便可見一個嬌俏的侍女,提著掃帚追著他們那英明神武的王爺,四處逃竄,而王爺卻又對那侍女百般偏袒。就在這時男主大人從天而降,安汐看著躲在男主身后的傻弟弟,氣不打一處來。某男“汐兒,你怎麼能以下犯上?”安汐“我這是家務事。”某男頓時臉一沉“你和他是家務事,那和我是什麼?”安汐“……我們也是家務事。”
56.6萬字8 483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