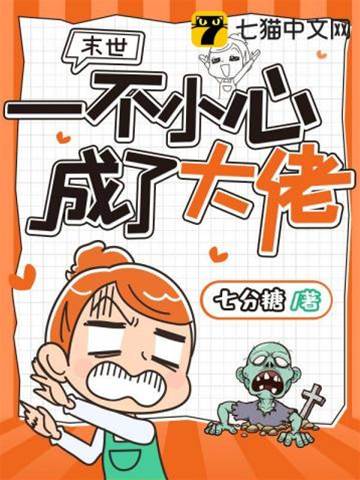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邪惡上將》 013.王子族
進那偌大的豪華房間後,南七夜被狠狠地丟到了的沙發上!
雖然不疼,但心裡卻極憋屈,的小臉像擰了結的麻繩,皺在一起,形了苦瓜形狀!
一記清脆的口哨聲響從旁響起,男人溫雅的聲音淡淡地傳開:“加繆,要憐香惜玉啊!”
本來這話,該是勸導那個對作惡的男人,可這刻聽七夜的耳中,卻儼然爲了揶揄的調侃味道!擡眉,沿著聲源看了過去,但見一張年輕而俊雅的臉呈現眼前,他的模樣帥氣人,但更讓人吃驚的是那渾上下出來的高貴氣質,表面看,似是親和,實際,那人舉手投足間的凜冽氣勢卻無法容忍他人輕易接近!
眉尖兒不由揚起,那彎出來的弧度,比例完,如初升的皎潔新月,令人沉醉。
“沒想到近距離看你,更加緻可人!難怪我們一向不近的阿爾伯特上將,居然也破天荒地要了你!”對上七夜那雙純黑的眼睛,費爾角斜斜一勾,笑容淺薄:“嗨,,我是費爾·伊·安德烈!”
Advertisement
即便來這裡的時日不多,七夜對這個姓氏還是一清二楚!
皇族中人!
眸子一瞇,眼底磨發出來的芒一閃一爍,並沒有馬上去迴應費爾的言語。
心裡卻在思索著剛纔在逃跑時候遇到加繆的景——
加繆是上將,費爾是王子,他們此刻聚在一起,是結黨的一夥?
所以,剛纔在房間裡聞到的那些腥味兒,是加繆殺了人?
心裡一凜,激靈地打了個冷!
“小姐,你沒事吧?”斯亞一直在旁冷眼旁觀,乍見這樣的神,低聲了話:“還是說,被加繆看中,你還沒有緩過神來?”
加繆淡淡地瞥他一眼,好似在怨怪他多!他優雅地坐到了七夜畔,指尖倏地一挑的下顎,冷聲道:“在想什麼?”
男人的眸子好深邃,就像一泓幽潭,明明是很平靜的,但裡蘊藏著的危險卻迫人,好像能夠把人隨意就吞噬進去——
都惹著了什麼人啊?
Advertisement
七夜手往他的腕位用力一拍,眼睛對上他那雙足以勾魂攝魄的碧瞳,咬了咬牙。
“爲什麼是我?”承認自己的確長得不賴,但聽聞來這個拍賣會的都是非富則貴的貴賓,加繆該是明眼人,初遇時候就應該明白倔強,怎麼還要了呢?
本來就來路不明的,難道作爲王子族裡的一個員,他就不怕,隨時反咬他一口?
加繆似乎沒料到會詢問這樣的問題,那冷酷的眼睛,驟然有抹的冷泛出,邪魅到讓人驚懼——
接到他那好似要殺人的目,七夜心裡莫名一慌,咬住下脣便不由自主地往著旁邊退開去。
豈料,加繆高大的子已經籠罩了過來,當著費爾與斯亞的面,掌心一揪的領,好像老鷹叨小般把拎了起來,往著地面便丟下去!
屁~著地,七夜只覺脊樑一痛,渾的脈都隨之翻滾,難到眉頭深鎖!
加繆彎腰,手臂一抖,掌心從茶幾上方劃過,指尖握住了擺放在水果籃裡的鋒利刀子,毫不猶豫地往著子揮了下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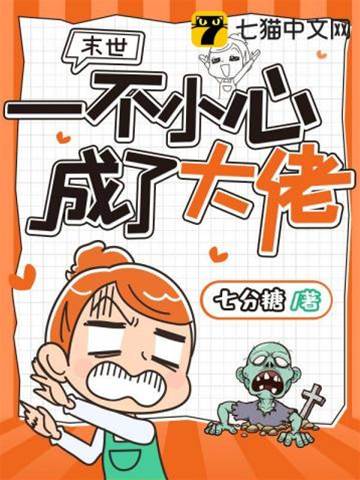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740 章

團寵大佬:真千金又掉馬了
林笙一出生就被扔進了大山里,被一個神秘組織養大,不僅修得一身好馬甲(著名設計師、格斗王、藥老本尊……),本以為有三個大佬級爺爺就夠炫酷了,萬萬沒想到,叱咤商場的殷俊煜是她大哥,號稱醫學天才的殷俊杰是她二哥,華國戰神殷俊野是她三哥,娛樂圈影帝殷俊浩是她四哥。某天,當有人上門搶林笙時:爺爺們:保護我方囡囡!哥哥們:妹妹是我們的!傅西澤一臉委屈:笙笙~我可狼可奶,你確定不要嗎?林笙:我……想要
131萬字8 269482 -
完結1602 章
丑妻逆襲夫人火遍全球了
云綰是被父母拋棄的可憐女孩兒,是她的養母善良,將她從土堆里救了出來。在漸漸長大的過程中,..
142.6萬字8.18 448598 -
連載424 章

咬色
爲了讓她乖乖爬到跟前來,陳深放任手底下的人像瘋狗一樣咬着她不放。 “讓你吃點苦頭,把性子磨沒了,我好好疼你。” 許禾檸的清白和名聲,幾乎都敗在他手裏。 “你把你那地兒磨平了,我把你當姐妹疼。” …… 她艱難出逃,再見面時,她已經榜上了他得罪不起的大佬。 陳深將她抵在牆上,一手掀起她的長裙,手掌長驅直入。 “讓我看看,這段日子有人碰過你嗎?” 許禾檸背身看不到他的表情,她笑得肆意淋漓,擡手將結婚戒指給他看。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71.8萬字8.18 13158 -
完結283 章

大佬的白月光又野又狂
不小心上錯大佬的車,還給大佬解除了三十年的禁欲屬性。盛晚寧正得意,結果被大佬一紙狀告,進了局子。她憤憤然寫完兩千字懺悔書,簽下絕不再犯的承諾,上繳五千元罰款……暗咒:厲閻霆,有種你別再來找我!……一年後。厲閻霆:“夫人,你最喜歡的電影今晚首映,我們包場去看?”她:“不去,你告我啊。”……兩年後。厲閻霆:“夫人,結婚戒指我一個人戴多沒意思,你也戴上?”她:“戒指我扔了,有本事你再去告我!”……五年後。厲閻霆:“夫人,老大已經隨你的姓,要不肚子裏的小家夥,隨我,姓厲?”她:“憑什麽?就憑你會告我?”……
72.7萬字8.18 132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